Description:“对于这种未知的等待,中国似乎非常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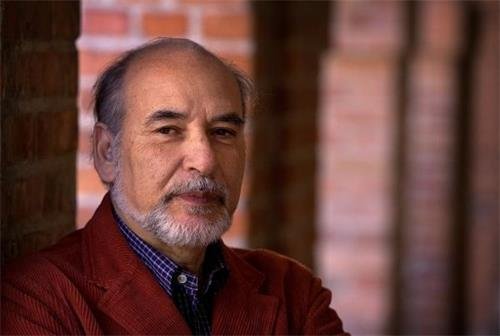
龚古尔奖得主塔哈尔:世界上只有一个种族——人类
地图上的摩洛哥,西濒浩瀚的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从15世纪末开始,摩洛哥先后遭受西班牙、法国的入侵,成为殖民地。摩洛哥独立之后,大量作家投身法语写作,以双重视觉观察北非阿拉伯地区及近邻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生态。
这其中,塔哈尔·本·杰伦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塔哈尔1944年出生于摩洛哥古城非斯,先后入读古兰经学校、阿拉伯语和法语双语学校。随后在法国学习社会学、心理学,并移民法国。
1987年,塔哈尔出版的小说《神圣的夜晚》,获得当年法国文学最高奖——龚古尔奖,成为北非阿拉伯作家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小说描绘了一个出身摩洛哥富人家庭的女孩,为继承家业,被父亲强迫当做儿子养大,扮演男人。父亲去世后,女孩被施行割礼,遭受家族迫害。《神圣的夜晚》直指摩洛哥社会宗法制度压迫下,女性悲剧的一生。这样一部揭疮疤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竟然获得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的褒奖。
1990年代后,塔哈尔的创作进入喷发期,矛头直指北非阿拉伯穆斯林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2001年,他的小说《那片致盲的漆黑》,获得都柏林文学奖。小说讲述了男主人公在摩洛哥沙漠地区的一座地下集中营内度过20年艰难岁月。有趣的是,这座专门关押政敌的黑暗监狱的建造者,正是为塔哈尔获龚古尔文学奖叫好的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虽然移居法国,塔哈尔还保留着摩洛哥国籍,每年有两个月回摩洛哥度过。一个真实的国度,多少虚构的故事,皆来自对那片北非沙漠的爱与恨。
3月18日,塔哈尔来到上海,与中国读者面对面交流,澎湃新闻对其进行了采访。
塔哈尔·本·杰伦。
“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紧密相连的”
澎湃新闻:您写作了多本教育学方面的著作,比如《向我女儿讲解种族主义》,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事这方面写作?
塔哈尔:这本书是教学用的书籍,但它不仅仅是教材,而且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书中涉及到不少我家庭的事情。我们出生在这个种族主义猖獗的时代,也时常爆发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运动。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什么是种族主义?什么是移民?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些移民?为什么大家不喜欢我的祖父?”虽然法国出版的书很多,但是关于种族歧视的话题关注非常少,所以这本书不仅是写给我女儿的,也给其他有着同样疑问的人。
澎湃新闻:有种说法“我们不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我们是变成种族主义者”,您怎么看?人为什么会产生种族主义观念?
塔哈尔:婴儿是不天然具有所谓种族主义的基因的,但如果每天告诉这个孩子,其他人与你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是黄色面孔、非洲人的肤色很黑……慢慢这个孩子就会变成种族歧视者。置身这样的环境,特别是在殖民地区,慢慢就会接受“有人是高于我们的、有人是低于我们”的这种观点。我想说的是,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不同种族的,世上只有一个种族:人类。
当第一个人类降临在这个世界,他/她会害怕第二个人类的降生,因为这意味着财产、资源被剥夺和被分享。我认为,种族歧视来源于这种恐惧。第二是陌生感,当我们不认识其他人时,会产生害怕和隔阂。但是不能因为种族主义现在很常见,就认为它是正常的,这是一种病。我每次到学校和孩子们讨论时,孩子们会问,这本书会让种族主义消退一些吗?很遗憾,我的回答是“不会”。
有趣的是,《向我女儿讲解种族主义》已经在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但没有得到中国任何出版社的注意,摩洛哥也没有。可能中国和摩洛哥一样,觉得自己的国家没有种族主义,种族主义都是法国、欧洲这些国家的事情。这是个有趣的现象,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紧密连接的,我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就有着很复杂微妙的感情,就像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一样。
澎湃新闻:在法国有句话“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不喜欢阿拉伯人”?
塔哈尔:这句话的原话是“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我不喜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还有一句谚语“种族主义者就像阿拉伯人一样,他们不应该存在”。即使在中国,大家也知道伊斯兰冲突这类问题。在法国,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了法国的第二大宗教,穆斯林几乎占了10%的法国人口。伊斯兰教并不是会反对法国民主自由的宗教,然而现在许多人提到伊斯兰的时候,就觉得这是罪恶产生的原因,我们把这种现状称为“伊斯兰恐惧”。宗教一直以来是被歪曲和误解的,伊斯兰教现在恐怕成了最不被人了解的宗教,伊斯兰恐怖主义者已经与经书的内容完全脱离了,变成了政治问题。
澎湃新闻:您对《查理周刊》怎么评价,他们对政治、宗教的讽刺力度是否过大?
塔哈尔:我很早就看《查理周刊》,而且有朋友在其中工作。我欣赏他们用夸张戏虐的手法去调侃政治事件。至于内容尺度的问题,我认为一份周刊,或者说任何媒体,都有自由说任何他们想说的话。这次的恐怖袭击,是对舆论自由的践踏,是对幽默和人权的践踏。
“作家应该去批评他所处的社会”
澎湃新闻:您早期的作品,如《哈鲁达》《孤独的遁世者》等小说描写了阿拉伯移民到法国、西班牙等欧洲近邻国家谋生的艰难和痛苦,您自己是否存在移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无归属感?
塔哈尔:我作为一个移民,自然而然会对移民身份、移民问题感兴趣,所以写了很多这类的故事。不过与大部分移民不同,大多数移民是体力劳动者,而我算是特权阶级、脑力劳动者,所以本身并没有经历他们那种痛苦,但能够感同身受,因为有着共同的身份,心的距离是很近的。
澎湃新闻:您最满意的小说是哪本?您写了很多揭露摩洛哥黑暗、腐败的小说,摩洛哥人民是怎么看待的?
塔哈尔:没有。我总是对已经写下的小说不满意,我觉得还能写得更好。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作家,其实不是一个好作家。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写得更多、更好。摩洛哥人民很喜欢我的小说,一个作家就应该去批判他所处的社会。我觉得要把批判精神传播得更广,让批判的声音走得更远。
澎湃新闻:您的小说中,存在着许多“女性观点”,有独特的女性化视角。
塔哈尔:是的,在我小时候,我看到我的姐姐、母亲、姑姑们整日操劳。在家庭的领主、父亲、丈夫回家之前,要把一切都准备好,周而复始。女性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却没有相应的自我空间和尊重,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在我第一步小说中,我塑造了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妇女的母亲形象。
澎湃新闻:您的小说《神圣的夜晚》获得法国的龚古尔文学奖,当时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还给您打电话祝贺了,能回忆下当时的情景吗?
塔哈尔: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国王打电话到我的家中,不过家中没人,所以没有直接对话。后来国王发贺电到大使馆,我礼节性地回复了他。摩洛哥大使非常惊讶,说“你疯了吗,怎
澎湃新闻:您有着双重国籍,就您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是法国人还是摩洛哥人?这两种身份会打架吗?
塔哈尔:这恐怕得用一把精密的天平来称一下,到底是法国人多一些,还是摩洛哥人多一些。多重的文化身份会让人更丰富,这对作家是好事。我用法语写作,但有时候会忽然卡壳,找不到对应的法语来描述我想写的东西。这时候脑海中会跳出一个阿拉伯词,吻合我的想法。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很多想法、观点、语言,还是来自摩洛哥。
澎湃新闻:您是个摩洛哥的“爱国主义者”吗?
塔哈尔:我当然爱摩洛哥,虽然现在大家不怎么提到“爱国主义”了,好像这个词过时了一样。摩洛哥南部的撒哈拉沙漠一带,和阿尔及利亚有冲突,阿尔及利亚人认为西撒哈拉是他们的,但事实上,西撒哈拉一直以来都是摩洛哥的。
经典童话再创作,希望孩子们了解世界上存在暴力
澎湃新闻:您也很擅长绘画,对《小红帽》《驴皮记》《蓝胡子》诸多经典童话进行了再创作,您是如何重新演绎这些经典故事的?
塔哈尔:我小时候读了很多童话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如何让孩子们通过故事去了解社会现实是我关注的,所以我再创作的童话故事颠覆了原有的故事结构。
比如我笔下的小红帽,她出生在一个需要妇女带着面纱的国家,“红帽子”变成了“红面纱”。她前往森林寻找外婆时,遇见的不是大灰狼,而是一个暴力战士(塔利班的象征)。她需要面对的是当一个男性暴力存在时,如何运用自己的智慧解决这个困境。这个战士杀死了外婆并假装外婆躺在床上,小女孩没有武器,她攻击了战士的生殖器,这个战士的生殖器非常小,小女孩把这个代表男性威力的器官打伤了。
我创作的《小红帽》,就是借用了经典童话,再加入现实元素,希望孩子们通过阅读,了解世界上存在的一些暴力,并保有宽容、警觉的心态。
澎湃新闻:写作与绘画是两项不同的艺术,您是如何从写作过渡到绘画的?您写作与画画的风格似乎是截然不同的?
塔哈尔:我非常喜欢笔与纸张摩挲接触的感觉。我写第一本书时,就像在画画一样。当我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在纸上画画用来排遣。从最开始即兴地画画,到后来慢慢给自己的画上色,再后来一有本子我就会画画。我有一个从事艺术管理的朋友,有一次他把我的画拿去放大制作成油画,这算是我正式介入绘画的契机。
和我的文学作品相反,我的画用色丰富,就像春天般的感觉,是没有艺术野心的,或者想要颠覆绘画艺术,这些都没有。如果说我的文学作品的基调是黑暗悲观的,那我的绘画风格可以说是光明乐观的。希望下次有机会带着我的绘画作品来上海。
“对于这种未知的等待,中国似乎非常习惯”
澎湃新闻:您来中国,是否感受了不一样的文化冲突?有什么给您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吗?
塔哈尔:我这次是有备而来,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介绍,所以并没有有很大冲突。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中国好像有很多工地,都在建高楼大厦,而一些矮房子在被推倒。中国似乎在走向一个不知方向的未来,我也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另外感到惊讶的是,我中国旅行期间时,有飞机航班延误了,在机场的十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广播却一直没有告知准确的起飞时间,对于这种未知的等待,中国人似乎非常习惯。飞到上海后,旅客们还鼓掌了,好像我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旅行一样。
澎湃新闻:您的作品中保留了许多口述文学的传统,似乎总有一个说书人在和您讲故事,您钟爱这种形式?
塔哈尔:对,叙事技巧上借用了这种方式。我在写作中会想象旁边有人坐着听我讲故事。有个读者曾经告诉我“在阅读您的作品是,我觉得这些故事都是听到的”,这是对我的作品最好的评价。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