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虎关》中乡村女性的出走与命运
王亚妮(甘肃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讲师)
[摘要]小说《白虎关》中,乡村女性大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着向往和憧憬。走出乡村前,她们都把将要走进的世界当成自己实现梦想的所在。然而,出走之后的遭遇迫使她们返回乡村,再次面对沉重的生活。乡村女性在离开土地后无路可走,返乡后要么死亡要么遁入虚空的结局是对乡村命运的隐射。面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洪流,乡村也经历着同样的无奈与无助。
一、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想的引领下发现了“乡村”[1],乡村女性以鲜明的形象出现在乡土文学作品中。但是,与城市女性和知识女性形象相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女性的关注、描写和思考略显单薄。当时,“娜拉出走”作为城市女性面临的复杂境遇成为文学界思考和讨论的对象,而乡村女性形象要么像翠翠那样,集真、善、美于一身,成为想象和向往的对象,要么像祥林嫂那样,被残酷的生活压迫、折磨,成为怜悯、叹息的对象。新中国成立之后,城市和乡村的女性生活状态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形象还是不能脱离乡土社会的伦理。贺仲明认为“‘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关联着勤劳、善良等优秀的传统乡村道德品质”,改革开放以后,“以‘土’为美的倾向迅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对‘洋气’特征的展示。”[2]在这里,女性外表的特征不再是“大眼睛”“大辫子”的健康美,而是换成了优雅、时尚的现代之美。这种对“洋气”的追求,在文学中表现为乡村女性对城市及城市女性的仰望姿态。城市成了乡村女性的向往所在,也成了她们走出藩篱,追求自我的动力。反映在文学世界里,八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集中地出现了“一个出走的女性形象群落”,“她们的出走标志着农业村社凝滞坚固的家庭模式、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土壤的大幅度松动乃至崩塌”[3]。
雪漠“大漠三部曲”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历时二十几年,直至 2008 年《白虎关》定稿,终于完成。它书写了世纪转折时期腾格里沙漠边缘一个小村庄的生活。这些故事里的女性代表了在经济发展、社会变革时期乡村女性的普遍生活状态。年长的女性继续生活在传统道德伦理所规定的身份状态下,她们虽然看到或者听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是乡土生活礼法的规约和十年来生活的惯性决定了她们与外界的隔膜感。年轻的女性具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追求,她们对乡村的感情更加复杂。这些女性的经历集中地体现在《白虎关》中。

二、女性对乡村传统的遵从与离弃
在乡村社会中,土地及由维持土地生产所衍生的婚姻和劳动力需求决定了乡村女性与土地的紧密关系。由于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由此所产生的相关礼俗更具约束性。它们将女性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作为劳动力及劳动力的生产者,她们无法轻易离开土地。表现在文学中,既有“你耕田来我织布”这种积极和谐的画面描写,也有逃离土地的挣扎。改革开放后的文学中,“工商业文明浸入农业文明,使得原有的地方性风俗变得松弛”[4]。面对新的环境,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对乡村及其传统呈现出不同的态度。
在《大漠祭》中,外面的世界通过电视进入乡村人的生活,拓展了他们的想象世界。到了《白虎关》,外面的世界随着机器的轰隆声走进了乡村人的真实生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母亲辈的女性囿于传统礼俗的规约,自觉地承担了传统乡村赋予自己的各种义务。她们生儿育女,将自己的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家庭中,同时,甘愿忍受“自家男人”的拳打脚踢。母亲辈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可以被认可为一种美德,但是当它们因固执的坚守而违背他人意愿时,则成了一种愚昧。这其中,灵官妈是前者的突出代表,莹儿妈则是后者的代表。
灵官妈身上集中了传统乡村女性所有被肯定的特征。她勤劳、刚毅、善良、通情达理。她容忍了老顺年轻时候的背叛,与他一起一心一意把孩子们养活大。虽然有时候难免有那个时代乡村女性的狭隘想法,但是,在读者眼里,她善良的本性掩盖了这些不足。在孩子们成年之后,她并没有过多地干预他们的生活,而只是在默默地尽己所能,把家里的生活维持好。因此,她跟莹儿之间没有常见的婆媳矛盾,跟儿子之间也做到了互相体谅。
与灵官妈相比,莹儿妈代表了乡村的另一群女性,她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农村妇女的性格局限性。她能说会道,也善于传播流言蜚语中伤他人。她一味并毫无底线地认同儿子的行为,对儿媳则处处刁难。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使她最终将女儿莹儿逼到绝路,酿成悲剧。归根到底,莹儿妈的这些行为是艰辛的生活和对丈夫的失望所造成的。莹儿父亲一直在做白日梦,梦想自己有一天能发大财,并为之到处奔走。因此,没有人能够分担生活的重担,莹儿妈只能靠自己。儿子成人之后,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即使在儿子毒打妻子,害死孙女之后,她依然护着他。这种迂腐的自私蒙蔽了她的善良,从而导致了她对女儿诉求的忽视,最终,葬送了莹儿的性命。
总之,年长女性们盲目地遵守着乡村传统,她们自身无法分别这些传统的优点和弊端,无法提出质疑,只能顺着生活的磨道低头往前走。
与母亲辈对乡村传统的自然遵从相比,女儿辈们对于乡村的情感更加复杂。莹儿、兰兰和秀秀都没有表现出对外面世界的强烈期待,也没有对现实生活方式的厌恶。花儿给莹儿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抒情的世界,在其中,她与自己的各种心情融洽相处。灵官给了莹儿最大的满足和永恒的回味与向往,因此,她可以坦然应对乡村生活中的各种艰辛。面对灵官的出走,她虽没有怨恨,但有时也难免会责怪那广阔的天地为什么窖不下灵官那份不安分的心,希望灵官看到家乡的宁静和纯美。
兰兰饱受了家庭暴力的伤害和丧女之痛。她鼓起勇气回到娘家。在修行中,她对生命有了新的理解,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秀秀作为双福女人,对双福在城市的生活充满了厌恶,不管是在双福发达前后,还是在其破产前后,她都坚守着自己乡村的家。在她看来,城市与肮脏脱不了干系。相比之下,月儿对于这种“老是吃啊,穿啊,平地啊,割田呀”的生活厌倦了,觉得“像磨道里的驴,转了一圈又一圈,没个尽头……”她“真想出去蹦跶一下。”[5]84虽然莹儿不赞同月儿对家乡的嫌弃,但是在月儿离开道别时,她也有些动心,想象自己如果能有不同的选择,也许一切都不一样了。
尽管几位年轻的女性对外面的世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她们的生活都受到了那个世界的影响,只是程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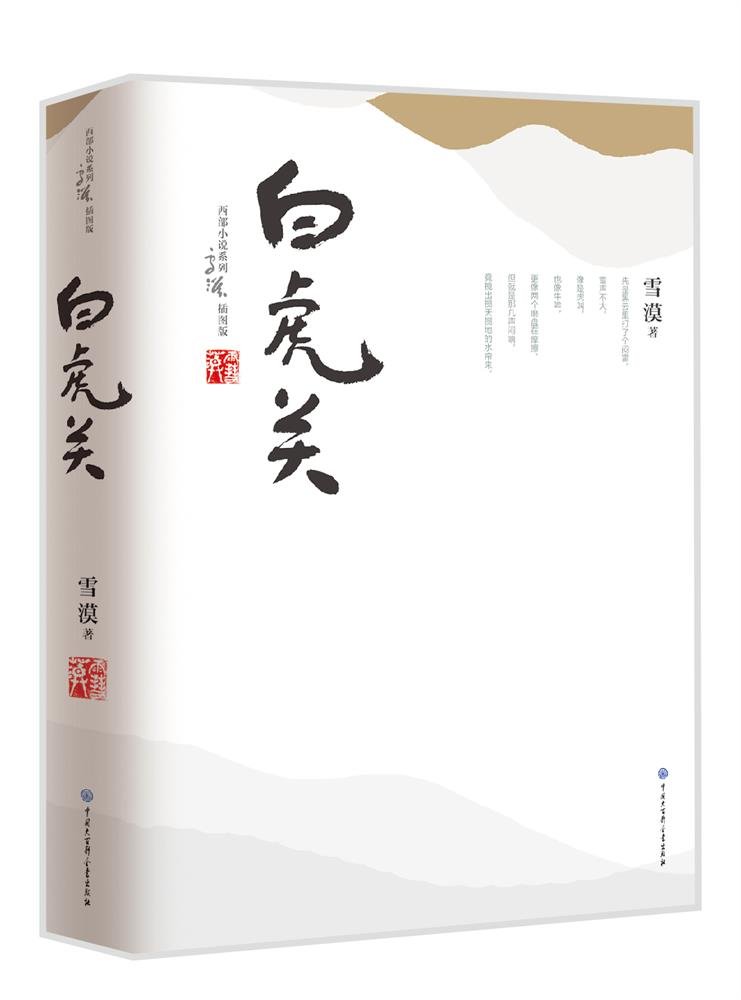
三、乡村女性的离乡出走
女性出走在近现代文学中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娜拉的出走在世界文学中引起了一场波澜。《新青年》专号介绍《玩偶之家》之后,中国文坛所塑造的一系列娜拉的姐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出走。面对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她们勇敢地走了出去。但是,走出之后,她们面对的依然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这样,这场出走便好似成了一场闹剧。鲁迅曾在1923年发表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为冲破封建家庭牢笼离家出走的女性提供了两个结局:要么堕落,要么回来。他笔下的子君应证了后一种结局。半个多世纪之后,《白虎关》中出走的女性依然摆脱不了类似结局的魅影。
月儿的出走想法是最坚定的,她把这一切归结为“一念书,知道的多,烦恼也多。”[5]84最终,在跟莹儿学会了所有的花儿令后,她走出了沙洼,去兰州城里找寻自己向往的生活。
与月儿的主动出走愿望相比,莹儿和兰兰的出走是被迫的选择。结婚前,莹儿将摆脱家庭困扰的希望寄托于婚姻和丈夫,丈夫去世后她又寄希望于爱情,在灵官离开之后,她只希望能守寡,照顾孩子。在这个希望都要落空的时候,她做出了积极的选择:自己挣钱给哥哥娶媳妇,这样“妈就不会逼她了”[5]238,她也可以守住自己想要的生活。
兰兰第一次出走是离开家暴的丈夫回到娘家。在娘家,她依然依赖着父母生活。为了不给婆家留口实,她决定和莹儿一起挣“赎身钱”。在这种背景下,莹儿和兰兰牵着两头骆驼,带着家什,穿越沙漠,前往盐池。
走出乡村之前,几个女孩对预期生活的想象是单纯的。月儿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所有的花儿令,再练练火候,肯定会唱得跟莹儿一样美。莹儿和兰兰也以为只要自己肯努力吃苦,肯定能挣到钱。她们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怀揣的想法肯定可以帮她们实现向往的生活。然而,现实远非美好。月儿在兰州以为可以寻到理想的爱情,最终却被染病,只能带着病痛返回家乡。兰兰和莹儿的遭遇则更凶险,虽然她们在沙漠里躲过了豺狗子,但是到了盐池,她们亲眼目睹了善良的大牛不明不白地死去,经历了头儿依仗自己的财势向莹儿的各种示好,她们不想“干些昧心事”[5]498,也不想屈从头儿的要求,最后牵着骆驼走进了沙漠,再次经历沙漠的凶险,回到家。
纵观这三位女性的遭遇,她们的出走和走出后的遭遇都与她们的女性身份密切相关。因为女性身份,她们不堪忍受乡村带来的种种裹挟和压抑,尝试逃离乡土。然而,在逃入的环境中,女性身份成了她们实现出走目的的羁绊。月儿染上了性病,莹儿因为头儿的纠缠不得不回家。这是女性出走后的困境。她们有了独立的想法和意愿,但是社会对她们的认可依然以性别为前提,她们无法摆脱性别局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得到认可。因此,即使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她们依然没有逃脱鲁迅先生所预言的要么堕落,要么回家的结局。

四、乡村女性返乡之后
在鲁迅先生的笔下,跟着父亲回家的子君,胸中充满了失望,回家的路是一条绝路。在《白虎关》中,经历了出走的不快遭遇之后,几位女性的唯一出路也是回家。她们的归途就像她们出走时的经历一样,充满了凶险。然而,出走时,她们心中有盼头,再次回家之后,“盼头没了,梦破碎了,只留下遍身的疲惫和伤痕”[5]505。她们面临着跟子君相似的境遇。回到沙湾村,月儿发现,曾经记忆中那个“一想到它,一晕温水似的东西就会在心里荡”的村子变了,城市里“那冰冷的庞然大物,也追到家乡了。”[5]360城市化的建筑破坏了乡村的安宁,但好在乡村灵魂的淳朴弥补了月儿身体的创伤。猛子对月儿的爱护,婆婆对她的宽容,以及生命尽头时村里人由怜悯而生的关爱都让她的心里充满了温暖,最终带着自己的美丽离开了这个世界。
月儿虽然带着备受歧视的疾病回到了家,但是,很幸运,她获得了丈夫和父母的关爱,与她相比,莹儿回家意味着被逼到生命的尽头。婆婆害怕失去孙子,时刻提防着她,母亲只想用女儿的婚姻换回给儿子娶媳妇的钱,她对简单生活的向往成了一种奢侈。最后,清凌的莹儿为了自己的坚守,在结婚当日吞下鸦片,结束了生命。只有兰兰,看透了生活的虚妄,在修行中找到了平静。
纵观这三位想要通过出走改变生活原貌的年轻女性,她们出走的资本是最淳朴的,也是与乡土直接相关的劳动力和花儿令。但是在面对商业化的外界社会时,她们的资本都失去了价值。淳朴和坚韧不怕苦的性格没有保证莹儿和兰兰赚来“赎身钱”,获得选择生活的权利。同时,城市里没有人理解花儿令的美,也没有人欣赏月儿的单纯。城市和它那些冰冷的庞然大物让这些清纯的农家女子伤痕累累。
当城市的冰冷蔓延到乡村后,最先受到影响的是人的想法。老顺像往年一样将自家的沙枣送给邻人,别人却怀疑他别有企图。他还没来得及适应人心的变化,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地,因为村子里最好的地被建成了游乐场。面对这些,村民们只能守着心里的惶恐。乡村就这样一步步地被城市化侵吞,一步步放弃了自己的坚守。它们的无助和无奈像极了乡村女孩步入城市的遭遇:只能退让,别无选择。
回顾历史,20世纪初,城市女性为争取独立而开创了中国女性出走的先河。虽然出走的结果常常不如人意,但是,她们的精神激励了中国女性,成为乡村女性的向往之处。与她们的经历相似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凭借其发展活力成了整个乡村的向往。然而,当乡村真正走进这种向往时,或当这种向往关照乡村时,没有美好的相遇,只有乡村的惨痛遭遇。
五、结语
乡村女性在离开土地后,如何才能独立并有尊严地生存?小说中没有给出答案。面对城市的强势发展,白虎关除了一步步地退让,还能为自己留住什么?小说同样没有给出答案。作者雪漠在《白虎关》第三版的序言中说:“农耕文明日落西山,大势所趋。……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5]7。小说的责任在记录,不在解决问题。这几撮碎屑已足够我们久久地思考。
面对势不可挡的城市化时,想要离土出走的女性和她们想逃离的乡村都成了弱者,她们没有退路,如果执意想要守住自己的本真,只能选择死亡。为了守住内心的美丽,两位年轻的女性没有拒绝死亡。可是,面对现代化的轰隆声和一座座树立起来的建筑,伤痕累累的白虎关会失去什么?又能守住什么?今天,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在历史中书写。
参考文献:
[1] 李静. 悲悯:当代女性乡土小说的文学特征[J]. 文艺研究,2015(11):75-81.
[2] 贺仲明. 观念与形象的多元变迁: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美[J]. 小说评论,2022(1):77-88.
[3] 丁帆陈霖. 重塑“娜拉”男性作家的期盼情怀、拯救姿态和文化困惑[J]. 南京大学学报,1995(2):67-107.
[4] 项继发. 重拾乡村社会记忆[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6-26.
[5] 雪漠. 白虎关[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
——发表于《河西学院学报》第38卷第六期(2022)
作者简介:王亚妮,女,甘肃庆阳人,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英语文学、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