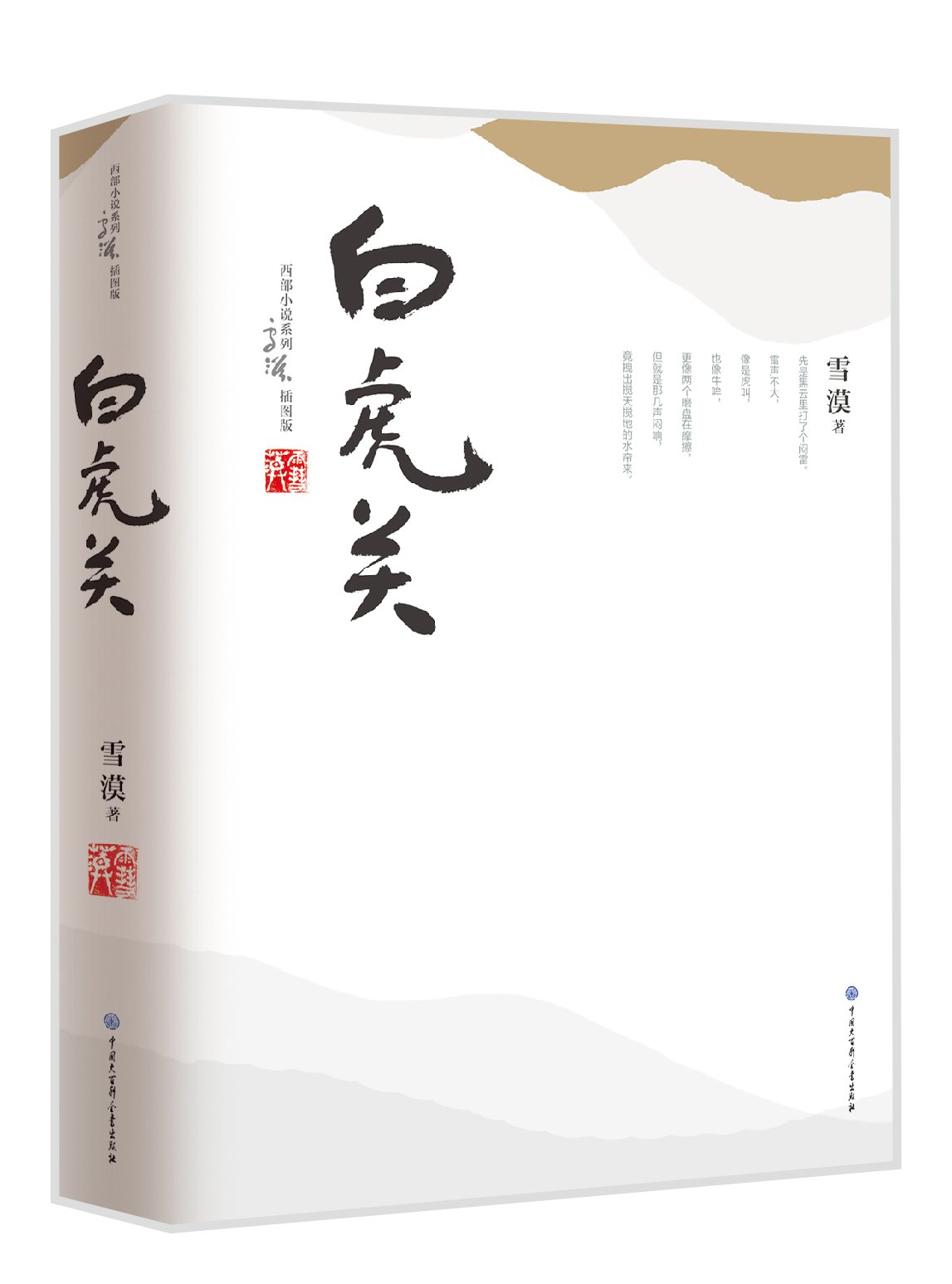
《白虎关》:现实与象征交融的生命苦旅
梁芬奇
【摘要】作为“大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白虎关》的独特之处在于,相较于《大漠祭》,其乡村生存哲学的精神内涵更近了一层。不只是写法上,而是对人的信仰,人的精神,人生存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探索。因此,《白虎关》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内容上也是“老顺一家”生活延续,但是却能深入到人的精神层面,在细致刻画乡土生活的同时,运用大量象征的笔法,借由对生命苦旅的开掘实现了别具一格的灵魂书写。
雪漠是新世纪崛起的西部小说作家。从坚实书写西部生活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大漠三部曲”)到艺术想象丰沛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灵魂三部曲”)和《野狐岭》,雪漠不断在文体和内容上进行新的尝试和突破。然而,最能体现其乡土情怀和心灵感悟的作品还是《白虎关》。正如雪漠所说 :“它用了最多生命积累,耗了最多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重读写实与象征特征同样明显的《白虎关》,正是探索其乡土题材作品深层意蕴的一个着力点。

一、写实笔触下西部农民生活的横断面
《白虎关》是西部文学乡土小说的代表作。正如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所写 :“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伊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交混的时代文化语境中,中国乡土小说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对它的概念和边界重新予以厘定就成为中国乡土小说亟待解决的问题。”雪漠笔下的沙湾,和急剧变化的外部社会相比,似乎显得有些封闭和停滞,但即便如此,沙湾依旧严酷而不失温情,而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
(一)风俗画式的人物塑造展现出西部地区独特的风土人情。雪漠一直以灵魂写作见长,但他的作品中却从未缺少地域文化的魅力,他更希望自己做一个“西部的文化志愿者”。《白虎关》写实着力最深处便是那些俯拾皆是的乡村生活图景。例如,猛子和齐神婆去相亲,路上遇见凤香和北柱打趣的情景。
凤香笑道 :“不行了,老了。你可得把眼珠子拨亮,别弄个猪不吃的茄莲来呀。”北柱接口道 :“就是猪不吃的,人家眼里,也是天仙呢。人家猛子不挑食,老的,嫩的都能啃。是不是,齐家干妈?”神婆笑道:“人家瞅的,是地道的天仙呢,红处红似血,白处白似雪,哪像凤香,丢尽牛粪里,也寻不出个眉眼。”猛子道 :“谁说寻不出来?比牛粪黑的,比牛粪臭的,肯定是她。”
这一段对话暗藏“机锋”,但读来又不失农民特有的朴实和幽默,特别是那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用词,充满了泥土气息。比如,“把眼珠子拨亮 ”“猪不吃的茄莲 ”“老的嫩的都能啃 ”“比牛粪黑”“比牛粪臭”这些语言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是地方文化和方言相结合的一种语言尝试。另一位山西女作家葛水平在《喊山》的开篇也有一段饶有兴味的对话描写。韩冲隔着山向琴花喊出什么时候“混插豆”,琴花想的则韩冲要“绕着山脊来自己的身上欢快欢快。”对话中“混插豆”的真实意义是曲隐的,需要稍加思考才能会意,而《白虎关》中“老的,嫩的都能啃”却浅露直白。这样的表达方式也能从中太行、太岳、中条三山交汇处,对面相望却要“绕着山脊”才能相见的地貌中看到端倪,而一望无垠的大漠则赋予了西部人快意爽朗的性格和生新泼辣的语言。除语言之外,文本中对大漠、盐池、骆驼等西北风物的描写,也为读者构建了一幕幕别开生面的西部乡土的风情画。
(二)作品如实呈现了现代文明的逼近和农业文明的逐渐消亡。这是乡土小说中较为常见的主题。正如鲁迅《故乡》中的“我”所思念和企盼的“故乡”早已凋敝,故乡和“我”之间已经产生的隔膜。《故乡》中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的瓦解体现在“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上,而《白虎关》中乡土的消逝则更加外显。进城又返乡的月儿,一回村旧发现村子变了,突出了几栋怪模怪样的楼。
随后,沙湾人的劳动和消费的意识也悄然发生着变化。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开始在窝子上打工。虽然失去土地被迫成为工厂雇佣工人的农民不同,但是雇佣关系的确立确是资本入侵乡土的一个潜在的标志。而不少农家女也开始成为发廊里的点缀。例如,猛子和曾经的相亲对象菊儿在发廊中的偶遇,就凸显了这种变化。菊儿认为她“凭劳动赚钱,又没偷又没抢”不怕人笑。但是,这种看似公平的交易,却也存在“给人打工,三七分成”的“不公平”,况且还要忍受沙娃的搂和亲嘴。她们的人生哲学便是“将来,死就死,先开心活几年再说”。但与忍受贫穷相比,菊儿们并没多少犹豫就做出了选择。除此之外,曾经乡邻间和睦互助也悄然变为利益算计,这可以说是资本的侵入乡土后带来的更为隐蔽也是更为深刻的改变。总之,《白虎关》正是用文字为农牧文化的最后留下了一抹晚霞,写出了城市现代文明的冰冷和异质性,但又不失对乡土饱含深情的挚爱和关怀。

二、直面人性困境与苦难历程的象征意蕴
虽然《白虎关》中对农民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已有十九世纪经典小说的神韵,但是作为信仰者的雪漠却说:“我想‘定格’的,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陈思和也曾在研讨会上指出 :“我根本不认为这部小说是现实主义小说,它是象征的东西,它通篇都是美丽的,通篇都是象征的。”“通篇象征”虽略显夸张,但是从整体上看,小说的象征意味也是明显的。
(一)小说开篇就提出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地点“金刚亥母洞”和“白虎关”。之前有不少学者指出“白虎关”就是“女人关”是三位女性莹儿、兰兰、月儿共同需要面对的生命的困境。需要补充的是,“白虎关”除了是困境的象征外,它更是贪婪和欲望的象征。在金子的诱惑下,沙湾人有的抓住了先机,一夜暴富,如双福,大头,但却迅速被酒色财气吞噬,甚至,锒铛入狱,家破人亡;有的心理失衡,想和命赌一把,如猛子,白狗,竟干出偷粮食和挖人祖坟这样的缺德事,盘下的窝子骑了“石驴”,最终落得空欢喜一场。正如老顺所说:“最先消失的,是心的宁静。”双福们和猛子们的心,都在欲望这个“白虎关”面前扰动起来,失去了宁静。除了老一辈的老顺和孟八爷还能在欲望面前保持审慎的态度,大多数年轻人都已陷入漩涡不能自拔。
另一个与欲望和物质相对的精神和文化的象征,则是“金刚亥母洞”。相较于《白鹿原》中的宗祠是儒家文化的宗法制度在乡村的象征,“亥母洞”则体现了西部文化的深厚与驳杂。金刚亥母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位女性神祗,后世从印度和藏地前来朝拜的修行者络绎不绝,而洞中出土的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物则彰显了红砂岩洞下的沧桑与神秘。除此以外,“亥母洞”也是沙湾人宁静的精神家园。但讽刺的是,小说中除了兰兰将亥母当作真正的信仰,并借此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外,大部分人,如月儿妈、王秃子等,都是带着“做交易”的心态看待信仰。他们在“打七”时丑态百出,相互倾轧,导致“七天”的辛苦功亏一篑。而老顺更认同这些人是“吃饱了撑的”,他觉得猛子妈供亥母的燃蜡是糟蹋钱。由此可见,虽然亥母洞也是热闹的,但猛子妈们对“亥母”信仰并不纯粹。和“白虎关”是金钱和欲望的战场相似,“亥母洞”也成了洞察人性的舞台。即便如此,“亥母洞”和“白虎关”依然可以看作是“灵”与“肉”的象征。
(二)莹儿和兰兰姑嫂两人穿大漠贩盐的历程也象征义颇浓。这一段惊心动魄的生命苦旅是全书的核心。这段历程本身有很强的宗教感,让人联想到自古以来那些“舍身求法”的人。与之不同的是,兰兰的信仰是亥母,而莹儿的信仰是爱情。这种信仰有宗教的意味,但又不完全属于宗教。兰兰她想求的“法”表面上驮盐换钱,为莹儿也是为自己“赎身”,但实际上苦旅也是自我救赎的方式,是对超越苦难的向往 ;而莹儿对爱情的信仰也帮助她在绝望时,重新燃起生的希望,让她拥有了和豺狗子搏斗的勇气,也让她在面对死亡时放下恐惧,执意留下“莹儿爱灵官”的字迹。因此,信仰能给人提供是摆脱精神困境的力量,而人物精神困境的超越也是雪漠在《白虎关》中着力最深之处。
除宗教感外,苦旅的浅表下还潜藏着寓言和象征。正如《老人与海》中的老人象征着面对苦难百折不挠的坚强和勇气,《白虎关》中的勇闯沙海的两位女性也是坚韧和顽强的化身。沙漠中酷热,饥渴,疲惫,失而复得的骆驼无一不带有象征意味。而大漠中狡诈,凶残的豺狗群,也能轻易夺取她们的性命,让人联想到男性主导的乡土社会对女性的戕害也是无形的豺狗群。莹儿因为“长得比画上还俊”,先后受到不同男性的骚扰 :用榔头把捣窗户的猛子,被爹娘默许欺负她的徐麻子,在盐池劳动时的大牛,和想要将她占为己有的“头儿”,以及强娶她的屠汉赵三。兰兰则终日忍受白福的毒打,女儿引弟被丈夫遗弃在大漠致死。吃人的豺狗子和“吃人”的人无异,只不过一个直露,一个隐蔽,而后者又对女性精神的摧残则更为深重。
(三)反抗绝望是这段动人心魄的女性史诗的另一主题。历经千辛万苦的莹儿和兰兰还是没能实现“救赎 ”,和《老人与海》中的老人最终还是失去了大马林鱼一样,莹儿和兰兰没能挣到更多的钱,等待她们的依然是命运的安排。然而,莹儿和兰兰这两位坚强的女性对待命运的态度和老顺一辈“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的逆来顺受截然不同。这种反抗的方式也是象征性的。正如鲁迅笔下的过客,反抗绝望的方式是走下去,即便知道前面是坟。莹儿以肉体的死亡死来殉爱情,以反抗象征着俗世的“安分”,而兰兰则以对亥母的信仰实现了精神上的“救赎 ”。莹儿和兰兰用自己的方式“走下去”,直面生命的苦难和虚无,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对生命的关怀与思考。
参考文献:
[1]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6。
[2]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3.
[3]陈思和等:《让遗漏的金子发出光辉——雪漠长篇小说<白虎关>研讨会》,《文艺争鸣》,2010,24(3):55-66.
[4]张继红:《“大漠—人—乡土”的一体性书写及局限》,《文艺争鸣》,2013,12(3):126-128.
[5]雷达:《雪漠小说的意义》,《人民日报• 海外版》,2004-6-18.
作者简介:
梁芬奇,女,汉族,天津人,硕士,山西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学。
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