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我们必须阅读,哪怕单单阅读并不能很大程度地完成我们要完成的工作。但我们必须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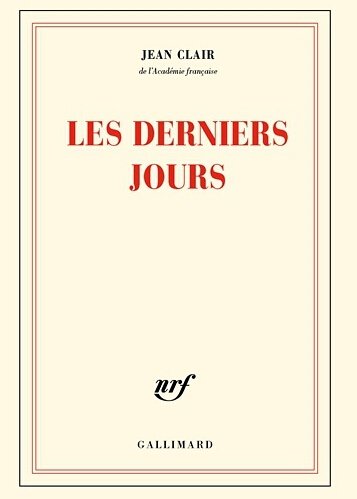
让•克莱尔:读,写
选译自Jean Clair,Les derniers jours,Gallimard,2013
让•克莱尔(Jean Clair):法国艺术批评家,2008年5月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曾长期担任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其著作《论美术的现状》(Considerations sur l'état des Beaux-Arts)中文版于2012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天该会一直暗着又下雨,细丝般的雨。这把我带回了童年,那时我发现自己被剥夺外出与同伴玩耍的权利,被囚在室内。窗户玻璃后,我去读、去写的欲望,被小小的水晶般的雨滴细密洒满了,它们在阴沉的灯光下,生长。
以前,阅读是为了减缓我的不耐烦,那样的阅读,是任意的。现在,阅读重新温热着内在的冷,这需要时间,也不能间断。
我们其实不在阅读,是再读——就像孩子要我们为他们再说一次那个故事,要确定还是那些人物、那些面孔,还是面临着那些危险,一页页地说着,同样的事物。孩童的我们观察着认为,大人,就是那些我们可以相信的人。然而当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人之时,却重复地在读,为了寻找旧时的情感和失去的时光。
再读,每个夏天都回到同样的房子,不用做梦也能重温那些习惯,继续从以前停下的地方读起,不需要寻找停下的那页,因为阅读在我们停止的地方自动开启,在其折页里折着的,是我们的回忆。
阅读曾是一种冒险,而再读则是回退。最大的幸福,是忠诚。今天有《追忆似水年华》,几个行段,然后是莫朗(Paul Morand)的短篇小说,穆齐尔(Robert Musil)笔下的维埃纳(Vienne),《大师和玛格丽特》,它们全如曾经读过的《小东西》、《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未来的收获》、《朋友的书》、《午夜飞行》……
(今天,这些书拥有怎样舒缓不安的力量?)
也许我们会知道,在一天渐渐过去后,窗户布满的一行行平行悬挂着的水珠就如老妇颈部,这个世上什么都没有改变。
“现在”,是灰色微薄的一层,在其下人事不再或消退。事物渐非,但书籍将之铭写,就像灰尘上轻印下的指印,总在那里,在同一个地方。技艺,还有比保证着这种永恒更好的存在理由吗?
(沿着日常及其缺口,这些书的目光从越来越远的地方打开,看着地下仍在不断流淌的水。)
确认那曾经发生——这意愿变得比因不耐烦而想去发现些什么更加迫切。那颤拂着神经,强制性的不安,挥之不去:我们回来读着,看那些我们已经好好读过的,想要控制;我们再一次翻动相同的书页,为了确证还是那些地方,那些人物,那些境况。
源于好奇,阅读曾是笨拙的冲动,没有目的,不求收效。而再读就像是下意识的一个仪式,犹如那转经筒,只需用手指推动,就可转动世界;又或像哄孩童入睡的老式音乐盒或风铃,酝酿着那些从荷马的故事或《罗兰之歌》(注:法兰西11世纪的史诗)就一直存在着的众神和英雄们:灰色眼睛的雅典娜,“牛眼的赫拉”,大卫,他的权杖和他的语录,查理大帝和他草丛般的胡子,罗兰和他的号角,珍妮和她的纺织机……
尽管如此,有时在我们信以熟知的文字里,却会显示出不同于那十五二十年前的意思:有了一种纵深,阴影与光都以不同的方式分布着,时间没有被抚平,而是更为深刻。
不同于在日间,夜里的光以别样的方式照亮事物:它勾画另外的轮廓,厘清另外的面庞,使大量的确凿无疑浮现,标出曾被埋没的脊棱,分层一直被混淆的视角。在一天的尾声里,它更暖一些。
唯一有价值的旅行,并非朝往别的风景,而是用新的视角看待过往。
敢不敢,然后,再添片言只语?
扎根在我身上的阅读强迫症——在对死亡及必须写作的恐惧面前——事实上就只像是一下轻咬,它是无害的替代品,一剂可爱的安慰剂。我们再读,为了确认曾经读过的一直都在。
而我们写作却是为了确认那些过往,我们好好活过。这又是另一种焦虑了。
再读源于对词语之恒定的起疑。这些年后,那些词语还有什么意义吗? 然而,尝试去写作,产生于对人对事存留的焦虑。所有这些人事在夜里袭来,让我不能入睡,却又可能从来都不曾存在过。一直都是那样,时间长到我都没有勇气去描述这种情况了。
对在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外貌记不清,我可以重新翻书,找到那个人的外貌描写与名字。然而记不清在过去是否经验过那样的时刻,是否认识过那样的人,是否承受过那样的情感……寻找与描述它们的痛苦就更大了,要做的也更难。
阅读,不过是“置身于形成中”,而我想被纳进读的运动里——就像在觉知自己的语言前,需要先随一门陌生语言的声响流动;就像一位作曲人,在创作前,先听几段旧时的大师之作,以求己调。
然后,那些遇见的面孔、遭遇的景色,与名叫Pierre、Philippe、Danielle 或者Barbara的人,以及被我不时记起的他们的笑容或言语——错位的、呼之欲出的——不再是幻想。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再次呈现,仿如曾经那般,也为了好好存在。
书桌上的小摆钟,声音晶莹,在我眼前一下又一下地数拨着时与刻。不像被无限再读的书陈列众神和曾经的传奇英雄;它像在斯特拉斯堡,在那天主教堂的天文钟,那时死亡以其指针踏数在一个流浪汉身上——踏数着同样的时与刻,这时于我房间内的同样时刻响起,但这次陪伴的是对生命中四个年龄段的巡视,从童年一直到暮年。
所有的回忆,都是死后的回忆。必须首先感到已经在自身中死亡,才能明白和回应那些不复在我们身边的声音。可能正因如此,人们认为回忆录作者有某种神秘的才能,他们能更好地理解当下,甚至有时能预知未来。
于是,我们在写作时,需要寻回那些安静阅读中读到的词语的轻盈。那些词语,从物质世界的沉重中解脱出来,有时甚至会在半寐中跌宕,就像夜晚的鸟儿,一刹那间闯进了白天的明亮里。
将自己置于写作中,不要被它们标记——那些趋于沉重的词。把它们化为“半词”。不要使它们害怕,甚至不要惊吓它们。要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注意中抽离它们,就如用眼角去看别人一样。更不可在这里驻留注意力,这会增加压力。要能够着力于他处中写作。那么词语,安心下来相信我们,便自来其意。
夜里,我躺在床上,身体卸去了重量,不动如在床单上悬浮,词语便会一个又一个地出现,不需要被特地寻找,就会自我精确,自我发音,猛然坠入我的脑里。然而,模模糊糊中,我想在纸上将它们记下的尝试只是徒劳。仅仅是简单地支起身子,移动手,便又是一番承重。身体重新变得有重量,钉住地上这些轻盈、准确、完美、在我脑海起舞的词语。它们不再动了。而早上我将会忘记它们。
写,就如读一样:我们为了逃离时间,忘记事物的沉重,然而,也在同时确证着时间的存在。
重复。再读。重新拥有。重新开始。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再置身于童年。孩童们重复着他们的故事,为了占有时间;老头们重复,为了消磨时间。
重回学院,在我离开的六十年后。
(然后,作为结束,再读难道不是一个这样的姿势,甚至在童年时就已经将我与宗教、与那联结我和众神、和世界的relegere(注1)关联起来?难道不正是那个姿势,在无尽地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的同时,在祈祷的呢喃中把我与它们联系起来?而阅读,在今天,却使我与之远离。)
《在读之时,在写之时》——于连·格拉克(Julien Gracq)忽略了以前就铭刻在学校墙壁中那无形法律的第三个指令,“计数”。
计数,为了以后衡量剩下的时间。每一被编码的书页让书成为一个计时的沙漏,词语是那细沙。除了用于阅读的时间,不再有其他的时间被计量;在此同时,除了阅读的时间,不再有其他的时间被释放。儿童故事的魅力就是如此,它既是故事,而在那唯一的如阅读般的愉悦中,不需要数着时刻,也已是对时间仔细的计量。
捕捉不可捕捉之事物,发音那些只在睡眠中可被听见的词语,在此努力中,事物的低语不可辨认,可能在第一时间,无法被听见。然而,它们也不可能被再语,不可以被更高声地说出,除非,在丧失了部分意义之后。而写作,就是如此一份无声的努力,充满重拾、内疚、遗憾和再语。
有些作者——一个朋友这样跟我说——写作是为了被再读,而不是被读。
不过还是需要有第一次的……喜欢再读的读者于是便优先成为那些写作为被再读的人的伙伴。
注1:Relegere,宗教(religion)的拉丁文词源之一,有“再读”(relire)之意。其另一词源religare有“连接”(relier)之意。
Ryk 译
译者笔记
这只是一本书里没有编码的某个篇章的第一部分。而这个篇章就名为《读,写》。让•克莱尔这本《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据他自己认为,书写了一个消失的世代,一个在他出生时占了法国百分之六十而现在仅存不到百分之二的世代。他说,必须承认的是,二十世纪的主要事件并非无产阶级的到来,而是农民的消失。
很多人评论这本书并没有写清如此深远的洞见,有的只是让•克莱尔普鲁斯特式的呓语。他谈论他的梦,他的童年,阅读之于他的意味,写作之于他的意味……而我之所以翻开这本书,当然只是因为那些只有真正年迈的人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那些最后的日子。
我对一个人最后的日子疯狂地着迷,同时间我还在读《维尔伦最后的日子》。我内心暗暗地可惜自己没有资格说这个词组,明明读着这本书于我而言也是让•克莱尔认为的“再读”:我在其中“再读”着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空间诗学》(La poétique de l'espace),或者更早一些的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的《另一个人》(Un Autre)。生活的每一瞬间都可以从木然突沉到质感氤氲的过去,这就是最后的日子。
不知道这本书会将一个年轻人带去何方。
我相信,“集”的参与者以及读者,都是喜欢阅读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以阅读为生”——我们必须阅读,哪怕单单阅读并不能很大程度地完成我们要完成的工作。但我们必须阅读。
然而阅读,在我自己情况,却慢慢地变成了一项强迫症——真的就像那种出门前死死捶几下门捶不开才愿意相信自己已经锁门了的那种强迫症。我希望让自己相信,自己“有在用功”。所以,“扎根在我身上的阅读强迫症,事实上就只像小虫轻咬——在来自死亡、来自“必须写作”的恐惧面前——它是无害的替代品,一剂可爱的安慰剂。”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