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我)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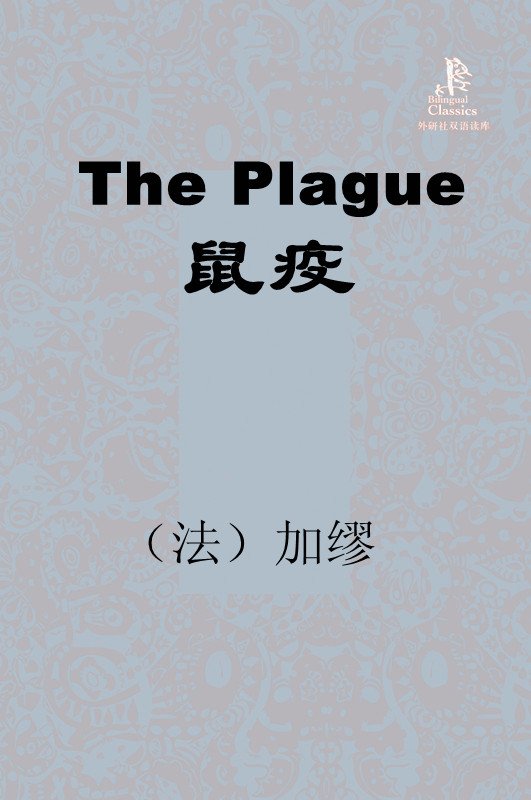
洪子诚:我的阅读史之《鼠疫》
洪子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专业著名学者。有著作多种问世。其中,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被有的学者戏称为“学界的红宝书”,影响之大可见一斑。他被学界关注的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学术成果的重要性和经典性,一是其个人“边缘性”的性格特征及其形成过程;而后者在他的《我的阅读史》一书中有比较深入的叙述。本文选自该书。
《鼠疫》与“文革”叙述
记不清是1981或82年,我第一次读到加缪的《局外人》和《鼠疫》。比较起来,我对《鼠疫》印象更为深刻。《鼠疫》的译者是顾方济、徐志仁先生,上海译文社1980年的单行本。因为有时还会想起它,在过了将近20年之后,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谨慎地谈到记忆中的当时的感动:“在那个天气阴晦的休息日,我为它流下了眼泪,并在十多年中,不止一次想到过它。”在这篇文章里我说到,读《鼠疫》这些作品的动机,最初主要是要了解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热度很高的“存在主义”。那个时候,萨特是众多知识精英、知识青年的偶像;“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是时尚的短语。加缪的名气虽然没有他那么显赫,但也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且也被归入“存在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的行列。当时,我对“存在主义”所知不多(其实现在也还是这样)。80年代是新知识、新学说、新方法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年代。从相当封闭的文化环境中走出来,求新慕奇相信是很多人都有的强烈意念。“文革”后我开始在大学里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课程,那时的“当代文学”地位颇高,负载着传递、表达思想、哲学、感性更新的“时代使命”。求知欲望与唯恐落伍的心理,长时间支配、折磨着我,迫使我不敢懈怠,特别是像我这样资质平庸的人。这种紧张感,直到退休之后,才有所松懈、减弱,也多少放下了那种“创新”的面具意识。
存在主义和萨特的进入当代中国(指的是中国大陆),自然并不始自“新时期”。“文革”前的五、六十年代,萨特的一些作品,以及国外研究存在主义的一些著作,就有翻译、出版;但它们大多不是面向普通读者,主要是供研究、参考,或批判的资料的“内部”出版物。萨特和波伏瓦1955年还到过中国。他们的到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亲近“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民主人士、进步作家的身份。五十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界对法国作家马尔罗、阿拉贡、艾吕雅,对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肯定性评价,大致也主要基于这一角度。1955年我正读高中,萨特他们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读过,好像只在《人民文学》上读过艾吕雅一些诗的翻译,也读过袁水拍翻译的聂鲁达的诗;最著名的当然是《伐木者,醒来吧!》。萨特和存在主义虽然五、六十年代已经进入中国,但当时的影响即使有的话,肯定也相当微弱;好像并不存在着相关思潮渗透、扩散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萨特在中国成为偶像式人物,要到“文革”之后。一般的解释是,经过“文革”,人们多少看到世界的“荒诞”的一面,但也竭力试图建立整体性的新秩序和思想逻辑:这样,萨特的存在主义凝聚了那些急迫要“走向未来”的人们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他们张扬个体的主体精神的情感的、理论的想象空间。另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是萨特在1980年的去世。受到关注的公众人物的去世,自然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正像加缪1960年因车祸去世在欧洲产生的反响那样,会更强烈地增加其关注度。中国一些感觉敏锐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适时地对其著作、学说做了有成效的译介、推广工作,萨特和存在主义热潮的发生便也顺理成章。
我虽然是抱着了解当时被“分配”到“现代派”里面的“存在主义”的初衷,而拿起《鼠疫》的。但作品本身很快吸引我,在阅读过程中,也就逐渐忘记了什么“主义”。在那个时候,我对加缪的身世知道得很少。《鼠疫》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阿尔及利亚北部海边城市的奥兰,但当时没有系统读过加缪的传记(况且较完整的加缪传记的中译本当时还没有在大陆出版),因此我不知道加缪就在那里出生,不知道他的童年在那里的贫民窟,在“阳光和贫穷”中度过。不知道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加缪参加抵抗运动的具体事迹。不知道他曾经否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不知道他和萨特之间的争论。不知道他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萨特却拒绝接受。甚至不知道他1960年1月3日死于车祸,年仅47岁。不知道和他翻脸的萨特在他死的时候写了动人的悼念文章。加缪是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的个人生活、行为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具有无法剥离的“互文性”。面对这样的作家来说,读者在种种背景资料上的无知,在作品感受、理解的“方向”和“深度”上,肯定会有不言而喻的损失。
但不管怎样说,阅读者的接受“屏幕”也不可能完全空白。相信当时的另一些读者也和我一样,会带着某些相同的东西(生活、文学的问题,情感、思想预期)进入他的作品。“自他去世以来”,人们总以“各自的方式,针对当时所遇到的问题阅读过他的作品”。八十年代我们的方式和问题,也就是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学写作的主题,即如何看待当代历史和刚过去“文革”,以及如何设计、规划未来的生活。因而,《鼠疫》的阅读,在我这里,便自然而然地和当时涌现的大量“伤痕”“反思”的作品构成对话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中国的“文革”记忆书写有助于发现《鼠疫》的特征;同时,《鼠疫》又影响了我对那些“文革”叙述的认识和评价。
加缪将英国18世纪作家笛福的话置于这部作品开首:“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鼠疫》是写实方法的寓言故事,它“反映艰苦岁月,但又不直接隐喻战败、德国占领和残暴罪行”[8]。虽然故事具有某种超越性,但读者也知道,它首先是“隐喻”那场大战,特别是战争中的占领和流亡。但问题在于,“文革”与二战之间是否可以建立起一种模拟性的联系?这是个至今仍存在歧见的问题。暂时抛开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不说,有一点应该是真实的,即“文革”刚结束的时候,这种联系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记得很清楚,1978年12月,北岛、芒克他们的《今天》的创刊号上,就刊载有德国作家伯尔的文章《谈废墟文学》;刊物编者显然是在暗示可以用描述二战之后的“废墟”“废墟文学”,来比拟“文革”的历史和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在以历史“灾变”的重大事件作为表现对象上,在近距离回顾、反思历史上,在叙述者赋予自身的“代言”意识上,在同样持有强烈的道德责任和承担姿态上,都可以发现《鼠疫》和当时的“文革”叙述之间相近的特征。我这里说的“近距离”,既是时间上的(《鼠疫》的写作开始于1942,写成和发表于1947,那时战争刚刚结束;读者看到的,是他们“刚刚度过的日日夜夜”),更重要的还是心理记忆上的。
历史创伤的“证言”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对萨特、加缪这样的作家无疑有一种亲近感,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介入文学”的主张和实践。“文革”后,主流文学界着力提倡、恢复的,是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到压抑的文学的启蒙、干预功能。那时,“纯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意识也已经在涌动,但支配大多数作家的,还是那种社会承担的意识。在这一点上,加缪这样的作家更有可能受到倾慕。他是一位置身于社会斗争、人间疾苦的作家,他的写作与关系人类命运的事件不可分离。在悼念文章中,萨特正确地指出,“他怀着顽强、严格、纯洁、肃穆、热情的人道精神,向当今时代的种种粗俗丑陋发起胜负未卜的宣战”。
伯林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19世纪俄国、西欧作家对待文学、艺术的不同态度,他以简驭繁(因此也不免简单)地称之为“法国态度”和“俄国态度”。他说,法国作家是个“承办者”,他的义务是写出他所能写出的最佳作品。这是他的自身义务,也是公众对他的预期。在这种情形下,作家的行为,私生活与他的作品无关,也不是公众的兴趣所在。而“俄国态度”则不然,他们信仰“整体人格”,行为、言语、创作密不可分;他们的作品必须表现真理,“每一位俄国作家都由某种原因而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众舞台上发表证言”。伯林说,即使“唯美”的屠格涅夫也全心相信社会和道德问题乃人生和艺术的“中心要事”。加缪和萨特是法国作家,但他们好像并不属于这种“法国态度”,甚至对法国文学传统的看法,与伯林也不甚相同。萨特在悼念加缪文章中,认为法国文学中具有“最大特色”的是“警世文学”。这主要不是对现象的描述,而是一种评价;这基于他那种更靠近“俄国态度”的文学观念。不过,他说加缪“顶住历史潮流,独自继承着源远流长的警世文学”,也可以见到这种文学态度在法国并非经常处在主流的位置。我对法国文学的了解肤浅,无法做出判断。但是,中国20世纪的新文学作家,在文学态度上与加缪,与19世纪俄国作家的相近和相通,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那些没有充分展示其生活和创作的“警世”姿态的作家,在大部分时间里,其道德状况在公众心目中总是存在疑点,他们自身也常存有隐秘的自卑感:直到现在,情形大概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在重大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历史事件之后,文学的承担精神和“介入”意识,首先表现为亲历者以各种文学手段,记录、传递那些发生的事实,为历史提供“证言”。这被看成“历史”托付的庄严使命,在由一种文化传统所支配的想象中,他们的良知被唤起,受到召唤和嘱托。亲历者的讲述,他们对亲历的体验、记忆的提取,在历史叙述中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呈现“历史面貌”的重要手段。加缪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在叙述的形态上,都特别突出“见证”这一特征。加缪在《鼠疫》中,就多次交代这部中篇的类似新闻“报导”,和历史学家“见证”叙述的性质。虽然是虚构性的寓言故事,却采用“编年史”的,逐月逐日冷静记下“真人真事”的方式。“见证”所标识的历史的“真实性”,是叙述者的叙述目标。因而,当书中说“这件事发生了”的时候,叙述者期待的是“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我想,中国八十年代那些“文革”的书写者,也会有相同的期待。因此,后来编写当代文学史,我便使用了“历史创伤的证言”这样的标题。这个标题试图说明这类写作的目的和性质,也提示写作者的身份特征和叙述姿态。
虽然有这些共同点,但我也发现它们之间的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作家(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和叙述的关注点等方面。由于加缪认为世界是非理性的,也怀疑那种历史“客观规律”的存在,以及人对那些“规律”的掌握。因此,他的关注点是人的生活,特别是在遭到囚禁、隔离的状态下,流亡、分离的不幸和痛苦;他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规律之前,而不是之后(虽然他也承认,当抽象观念涉及人的生死时,也必须认真对待)。也许那些艺术并不高明的,诸如《伤痕》那样的作品,也表现了将人的幸福置于抽象观念、教条之前的倾向,但是接踵而至的许多“反思”小说,就逐渐把关注点挪到对“规律”的抽取中,因而,事实上它们难以避免滑落进图解当代那些既定观念的陷阱。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是《鼠疫》叙述者清醒的限度意识。虽然叙述者认为是在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但也不打算让这种“代表性”的能力、权威无限度膨胀。从《鼠疫》的叙述方式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由于那时对西方现代小说技巧所知不多,我最初读《鼠疫》时,对它的人称和叙述方式颇感新奇;大概不少人都和我一样,所以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这个小册子,才会在文学界引起那样的强烈反响。开始以为是一般的第三人称叙述,感觉有点像海明威的那种简约手法。待到小说就要结束,才知道叙述者就是作品的主要人物里厄医生(“这篇叙事到此行将结束。现在正是里厄医生承认自己是这本书的作者的时候了……”)。这个本来应该显露的叙述者,却一直隐没在叙述过程中;也许可以把它称为“第三人称化的第一人称”叙述。这种设计,相信不是出于一般技巧上的考虑,而有着某种“意识形态”含义。这种个人叙述的客观化,按照加缪传记作者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他本人的反应和痛苦同样是自己同胞的反应和痛苦”,“他感到他是以众人的名义在说话”。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也是在为这种“以众人的名义”的意识做出限制,不让它膨胀成虚妄的夸张。其实,在作品中,对于这一“见证”叙述的限度,已一再做出说明。书中强调,叙述者“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因而叙述始终保持着“恰如其分的谨慎”。谨慎是指“避免叙述那些他自己没有看见”的事情,也指避免把一些无中生有的想法、推测强加给所叙述的物件。这是既以客观的姿态显示了他的“知道”,同时也以对“无知”的警觉显示“我不知道”。我推测《鼠疫》的作者有可能是在抑制第一人称叙述在抒情,在揭示心理活动、推测事情因由的各种方便,但同时,似乎也在削弱第三人称叙述有可能开发的那种“全知”视角:后者在加缪看来,可能近乎虚妄。
萨特在评论《局外人》的艺术方法的时候,曾有“玻璃隔板”的说法。他说,“加缪的手法就在于此:在他所谈及的人物和读者之间,他插入一层玻璃隔板。有什么东西比玻璃隔板后面的人更荒诞呢?似乎,这层玻璃隔板任凭所有东西通过,它只挡住了一样东西——人的手势的意义。”“玻璃隔板”其实不是萨特的发明,倒是来自加缪自身。在著名的《西绪福斯神话》和《记事》中,他就不止一次谈到过。当然,他是以此用来说明人与世界之间的荒谬关系,并不专指艺术手法的问题。不过在加缪那里,所谓“手法”与“内容”难以分开。这种“玻璃隔板”的方法,套用在《鼠疫》中自然并不完全合适,但它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应用。加缪在为《鼠疫》写作所做的笔记中写道,“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我)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里厄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并等待着观察、得知,正是《鼠疫》在叙述者与人物,甚至叙述者与他的情感、心理活动之间插上的“玻璃隔板”。它降低着叙述者(一定程度也可以看作是作者)认知的和道德的高度;不过,这种降低,其实也不意味着思想上的和美学上的损失。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