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雪漠依靠文学语言的独特能量,借助西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对“灵魂”进行复魅,重新恢复灵魂的活力,这是《野狐岭》所揭示的一个重要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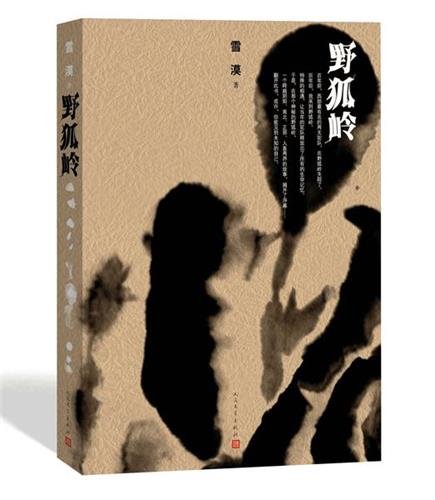
《野狐岭》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
《野狐岭》:灵魂的重量
文\王鸿生
雪漠的长篇《野狐岭》出版了,让我感到庆幸的是,雪漠仍是个小说家,他没有远离文学,去做专门的修行者。一直以为,是文学在多重意义上创造了雪漠,同时也牵制了雪漠,并将他置于文学与修行的巨大张力之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非常空灵的一面—这得益于他的修行经验,又能把众生的爱恨情仇写得元气淋漓,富有生命的质感—这自然得益于文学。
陈晓明教授当年有过一个很传神也很准确的说法,说雪漠的写作是“灵魂附体”。到了《野狐岭》,雪漠显然又进一步,有点“灵魂出壳”的味道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写作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关于灵魂及其叙述问题,是汉语叙事文学一向比较薄弱的层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斌的《一岁等于一生》、潘婧的《抒情年代》(写作期)等,已经从多角度尝试过灵魂叙事,尤其是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总体上看来,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的文学案例并不多。可以说,雪漠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灵魂叙事,有相当大的拓展和推进。
出版后,有评论说雪漠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智力的挑战。对于“智力”这个词我比较警觉,因为这将造成不必要的误读。雪漠的写作不是智力性的写作,他的小说也不是某种知性叙事,而确实是一种灵魂叙事,以一种非常直接的幽灵或幽魂的叙事,打开并复活了历史中长期被掩埋的失踪者的记忆。小说的每一次会话,人物的每一种动机、行为,都体现了他的这种重新历史化的冲动。但他又没有去寻找和还原一个所谓的历史真相,他对历史、对记忆做了伦理化的处理,而不是认识论的处理—当然,这跟他有宗教追求相关。他要处理的对象,无非是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矛盾,就像保罗·利科说的,记忆伦理的彻底性不是对记忆进行复原,而是对记忆中的罪错实行“沉重的宽恕”。雪漠做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释放了大量被压抑、被扭曲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一种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能,并和当代世界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自十九世纪以来,灵魂这个概念已被理性祛魅,人们用心灵、意志、意识、无意识等概念取代了灵魂,于是灵魂书写变成了心理描写。但灵魂这个东西真的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都会感受到那种强大的灵魂冲击力。在文学中,我们不仅遭遇到别人的灵魂,也会和自己的灵魂照面。这就是说,虽然现代科学否定了灵魂,或者说灵魂并非一个实体,但至少在文学中,通过言与心的特殊结合,我们也完全能感知到灵魂的在场。雪漠依靠文学语言的独特能量,借助西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对“灵魂”进行复魅,重新恢复灵魂的活力,这是《野狐岭》所揭示的一个重要命题。
转载:http://epaper.ynet.com/html/2014-11/28/content_99310.htm?div=-1
北京青年报201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