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沙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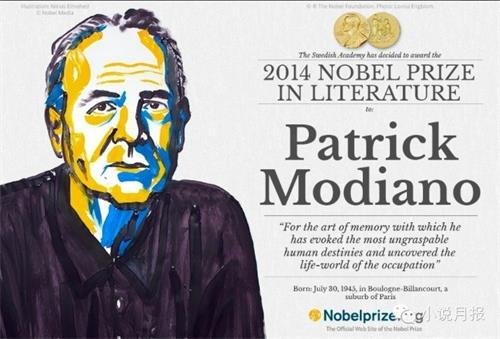
我们都是“海滩人”:莫迪亚诺的魅力
文/柳鸣九
柳鸣九先生从莫迪亚诺代表作《暗店街》(又译《寻找自我》《寻我记》)摘录的这一段,或可为读者进入莫迪亚诺小说世界提供一个入口:
“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所谓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在游泳池旁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里的一角或背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自己就是那种‘海滩人’。况且,即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沙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莫迪亚诺的魅力
文/柳鸣九
迦利玛出版社的福利奥袖珍本丛书开本甚小,排印得也很疏朗,每一行大约有十来个字,而莫迪亚诺收入这个丛书的几部小说,仅占一二行的文句居绝大多数,占三四行的文句已不多见,三四行以上的则极为稀罕了。这与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的“长句作家”的语言恰成鲜明的对照,那些“长句作家”,较远的有普鲁斯特、较近的有布托,往往一个文句就占一两页两三页,而且还是“七星丛书”本排印得密密麻麻的一两页两三页,或者是大开本的两三页,从句套从句,九曲十八弯。这种语言录像在莫迪亚诺的笔下是绝对没有的,他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从句,而经常用状语、补语与分词句,这就使他的文句简练到了几乎是最大的限度。
过份简练,就得防止平淡、单调与贫乏。莫迪亚诺可没有流于这种危险。他的语言很有涵量,很有弹性,很有表现力,很是传神。
请看:
这是描写一个乐队极其糟糕的演奏:“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滋”。一个多么传神的动词“折磨”(Tontnnait)!
这是写战争时期肃条的巴黎:“街上空空荡荡,是没有巴黎的巴黎”,Panisahsent这一个只带有一个形容词的名词,意味何其丰富!
这是写疲劳时的感觉:“是疲劳就像一只老鼠,把我周围的一切都啃得模模糊糊”,原文只用了十多个字就把一种难以言状的感受,铸造得如此生动!
这是写对城市的感情:“我喜欢这个城市。她是我的故乡。我的地狱。我年迈而脂粉满面的情妇”。这三个简单的比喻,包含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多么复杂的经历与感情!
这样的语言,既闪现着一种诗的才华,也体现出一种锤炼的功力。你读莫迪亚诺的时候,首先能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凝炼的语言美!就是这种语言的魅力。
莫迪亚诺的小说还具有一种情趣的魅力,使你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如果考究其因,那么,你也许会觉得是其中某种近似侦探小说的成份在起作用,至少在他最初几部使他名声大噪的重要小说里是如此。在《夜巡》里,一个青年人充当了双重间谍,同时为法国的盖世太保与地下抵抗组织效力,危险的差事使他的生活与精神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而读者也提心呆胆地看着他将有什么样的遭遇、他最终将如何解脱。在《魔圈》中,一个青年人打进一个形迹可疑、犯罪气息很浓的圈子,想要与陷于这个集团的父亲相认并了解他的过去,随着他的追踪,读者也一直想搞清楚这对父子的来龙去脉以及他们生活的隐衷。在《寻找自我》中(书名原文直译应为《暗店街>,现根据小说的内容意译为<寻找自我》),主人公在一次劫难中丧失了全部对过去生活的记亿,一些年后,他当上了一个私人侦探,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寻蛛丝马迹以求搞清楚自己已完全被遗忘了的前半生的真相,于是,读者也就被引入他艰难曲折的调查,关心着这个阿里阿德涅线团的每一个头绪。此外,在《户口簿》里,又有一个人的生平经历有待查清;在《星形广场》与《凄凉别墅》里,也有扣人心弦的逃亡与躲避。总之,莫迪亚诺小说里,老有某桩不平常的事件、某种紧张气氛与压力,老有一个与所有这一切有关的悬念在等着你,使你急于知道它的究竟与结果。
他的悬念与柯南道尔、克里斯蒂、西默农这些侦探小说大师的悬念不同,在侦探小说家那里,悬念是很具体的,只关系到一个具体事件与具体人的某个行为真相,而莫迪亚诺的悬念却是巨大的,笼统的,往往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的悬念(《星形广场》《夜巡》),或者是关于一个人的实在本质的悬念(《魔圈》),要不就是关于一个人整整一段生活的悬念、全部生活经历的悬念(《寻找自我》《户口簿》)。在侦探小说家那里,导致悬念解决的,是一个个高度戏剧化、高度偶合的具体情节与行动,而在莫迪亚诺这里,导向悬念最后结果的,则总是一个个平常的细节、淡化的场景,绝不会有枪声、血迹、绳索、毒药瓶,倒是在这些平淡的场景细节中,充满了当事人自己即自我叙述者本人充满了感情色彩的思绪,甚至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声。这样,在他的小说里,就有了评论家所指出的那种“紧扣人弦的音乐般的基调”,而到最后,与所有侦探小说中悬念都有具体答案的结局完全相反,莫迪亚诺小说的悬念答案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夜巡》中那个处于危急与困顿的双重间谍将如何结束他这种尴尬难堪的存在状态?《魔圈》中叙述者“我”所深情追踪的父亲仍是一个谜,《寻找自我》中的“我”总算挖出了一段被埋葬的生活经历,然而对自己前半生绝大部份的回忆仍然是一片空白。莫迪亚诺小说的结局有一种强烈的揪心的效果,与读完侦探小说时的那种释然的感觉截然不同,而且,它还留下了好些耐人寻思的余韵。于是,你会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莫迪亚诺的作品与侦探小说实有天壤之别,而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大有深意,如果说,莫迪亚诺有使你要一口气把作品读完的魅力的话,那么,他更具有使你在掩卷之后又情不自禁要加以深思的魅力,一种寓意的魅力。这对莫迪亚诺来说,是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显然也是他致力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
莫迪亚诺迄今发表了近十部小说,奠定了他在法国当代文学中重要地位的,正是他最初的两组作品:《星形广场》《夜巡)、《魔圈》与《凄凉别墅》《户口簿》《寻找自我》。如果对这些作品进行综合观察的话,那就不难发现它们往往具有相似的成份、相似的格局、相似的矛盾,而从这些相似中,又闪现着相近的寓意的光辉,它构成了莫迪亚诺在当代法国文学中鲜明的标志与独特的魅力。
从作品的历史背景来说,这些小说的故事几乎都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时期。在《寻找自我》中,虽然主人公是在战后寻找自己的过去,但他所找到的那一段过去,那一段悲惨的、使他丧失了全部记忆的生活,正是发生在第二次大战初期阶段。对此,人们不能不感到奇怪:莫迪亚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他毫无第二次大战时期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他偏偏一而再、再而三选了这个时期的生活作为他小说的内容?显然,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感受与第一手素材能写出像《海的沉默》《禁止的游戏》那样真切反映了大战时期生活的作品。他也无意于这样做。他在自己的小说里,很少对这个时期带历史标志的场景现像进行描写,只有《星形广场》有点例外,在它作为题词的小故事里,的确标明了“1942年6月”,还有“一个德国军官”也闪现了一下,小说的最后也有主人公在星形广场被处决的描写,这些总算带有明确的历史标记。在《夜巡》中,这种明确的历史标志有了淡化,除字里行间出现过“希特勒”这个名字外,几乎别无其他,在这里,身份明确的法国盖世太保也只是像一些模糊的阴影。到了《魔圈》与《寻找自我》中,这种历史真实的淡化就更加明显,在《魔圈》中,只有一个反动文人关于检举出卖犹太人的只言片语与几个把“父亲”抓走的“穿风衣的人”,这几个人比影子还模糊不清,而在《寻找自我》中,只有从主人公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与他一心要逃到中立国去的愿望,我们才能断定故事是发生在什么时代。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莫迪亚诺绝无从第二次世界时期摄取历史生活场景的意图,他只满足于借用这个时期的名称与这个时期所意味的那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直到战后很久还像恶梦一样压在法兰西民族的记忆里。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背景,在莫迪亚诺小说里,所具有的意义就只是像征主义的、而不是现实主义的了,而像征,正是最能包含寓意的形式与框架。
从小说的人物形像来说,莫迪亚诺几部主要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犹太人(《星形广场》《环城大道》)、无国籍者(《寻找自我》)与漂零的流浪者(《夜巡》),他们无一不承受着现实的巨大压力,莫迪亚诺从德国占领时期那里支取来的像征性的压力,就是压在他们的身上。《星形广场》中犹太人主人公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在法西斯反犹太主义的阴影下,惶惶然从法国躲避到以色列,最后在幻觉中被处决在巴黎的凯旋门前;《魔圈》中的犹太人“父亲”,一直过着暗无天日、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不敢与自己的儿子相认,最后仍然落进了魔掌;《夜巡》中的青年主人公陷于法国特务的魔窟,在周围阴森恐怖的气氛下,他艰难的双重生涯使他的精神处于时时都有崩溃危险的边缘,《寻找自我》中的彼德罗·麦克沃伊也无时不感到环境中危机四伏,夜晚,他经常灭了灯,躲在窗帘后面察看街上警察的动静。
在全面了解了莫迪亚诺笔下人物的存在状态之后,我们就逐渐接近莫狄亚狄的寓意。面对着黑沉沉的、看不见的压力与周围那种令人不安的气氛,面对着自己的存在难以摆脱魔影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些人物无不感到自己缺少存在支撑点、存在栖息地的恐慌,无不具有一种寻求解脱、寻求慰藉、找寻支撑点与栖息处的迫切要求,无一不具有一种向往“母体”的精神倾向,似乎是尚未满月的婴儿忍受不了这个炎凉的世界,仍然依恋着自己的胞衣。引人注意的是,母亲、父亲、祖国以及像征着母体祖国的护照与身份证,成为了人物向往的方向、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他们想要找到的支撑点,但他们的这种响往与追求无一不遭到悲惨的失败。《星形广场》中的犹太青年拉法埃尔·施勒米洛维茨怀着扎根的意图,到处寻找自己的栖息地,最后是以恶梦收场,《夜巡》中的“德朗巴勒公主”在严酷可怕的环境下,唯一使他感到藉慰的就是远在洛桑的妈妈,然而,要摆脱他所处的险境到妈妈那里去,却比登天还难,他最后只能以自己的生命去触犯死亡,走上了殉道者自我毁灭的绝路才结束他两难的存在状态;《魔圈》中的“我”,怀着深情,不畏艰难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但父亲却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只拥有伪造的“身份证”,他没有祖国,他还企望从儿子的一份中学毕业文凭中得到对他的根基的确认,就像一个将溺死的人抓住一根稻草;《寻找自我》中,不仅彼德罗是一个没有合法护照、没有正当身份的“黑人”,而且,弗雷迪、盖伊、维尔德梅尔也都是持假护照者,在法国没有正当身份,他们只能躲在边境上,伺机逃到中立国去,而这种冒险带来的却又是更大的不幸。莫迪亚诺小说中这样一个个故事,都集中地揭示了人在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根基的状态,表现了人在现实中得不到确认的悲剧,或者说,现实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悲剧。
仅仅是得不到现实的确认,而且更惨的是得不到自己的确认。莫迪亚诺继续深化自己的主题,在表现人物寻求支撑点、栖息所的同时,又表现了人寻找自我的悲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又一个深刻的寓意,也许是二十世纪文学中最耐人寻思的寓意之一。
在《夜巡》的结尾,那个双重间谍这样说:“我允许我的传记作者简单地把我称为‘人’并希望他有足够的勇气写出我的传记。”这句话,明确地标出了小说故事与人物的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个双重间谍身陷于两个对立营垒的夹缝之中,疲于应付两方面的压力,这种难堪的状态使他完全失去了自我,他甚至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对于法西斯组织来说,他名叫斯温·特鲁巴杜尔,对于地下抵抗组织来说,他名叫“德朗巴勒公主”,他的自我究竟是可耻的特务还是潜伏的志士?他最后的选择似乎是为了确定自己的性质,然而,你掩卷之后能完全确定他的自我性质吗?寻找自我的悲剧,在这部小说里已初见端倪。同样,在《魔圈》里,“父亲”完全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丧失了自我的形像,他既无真名实姓,也没有清清楚楚的经历,他身上裹着一层暖昧的浓雾,而他这种自我的丧失,正是与他支撑点的丧失、栖息处的丧失紧密相关的。叙述者“我”力图替自己的父亲恢复自我、显现自我,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而且,“我”本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形像,人们称呼他的那个名字,仅仅是他在旅馆登记簿上的一个化名,他替父亲显现自我的努力归于失败,也就等于他寻根溯源、寻找自我那一个重要部份的努力纯系徒劳,他将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这一部份自我。不言而喻,到了《寻找自我》称中,寻找自己的主题发展到更明确更清晰的程度,在这里,叙述者“我”几乎丧失了全部的自我:自己的真实姓名、生平经历、职业工作、社会关系,他成为了一个无根无底的人,一个没有本质、没有联系的飘忽的影子,一个其内容已完全消失泯灭的符号,而“私人侦探居伊·罗朗”这个符号仅仅是他偶然得到的,他真实的一切都已经被深深埋藏在浩瀚无边的人海深处,他要到这大海中去搜寻一段段已经散落的零星线索,他所从事的这件事,其艰难似不下于俄底修斯为了返回家乡而在海上漂流十年的经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创作了一部现代人寻找自我的悲沧史诗。
寻找自我,是一个深邃的悲剧性的课题,它不仅摆在莫迪亚诺小说中那些具体人物的面前,而且也摆在所有的现代人的面前,何况,莫迪亚诺笔下的“德朗巴勒公主”还曾要求把他视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也正因为这是一个世人都面临的问题,所以,他才把为他写一部确定自我、寻找自我的传记视为一件需要“足够勇气”的事情。在莫迪亚诺的作品里,确认自我、显现自我、寻找自我之所以特别艰巨,就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人都经受着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这种自我泯灭与自我消失,首先是发生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发生在“流通过程”中,在这里,不仅有严峻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种种原因促使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我泯灭、自我消失,而且,复杂的社会流通过程、现代复杂的生活方式也促使自我的泯灭与消失,正像《寻找自我》中的“我”所感受到的:“人们的生活相互隔离,他们的朋友也互相不认识”,于是,在开放性的现代社会里,频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实际上倒成为了这样一种情景:“千千万万的人,在巴黎纵横交错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就像无数的小弹丸在巨大的电动弹子台上滚动,有时两个就撞到一起。相撞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踪迹,还不如飞过的黄萤尚能留下一道闪光”。
也许更主要的是:自我消失、自我泯灭还取决于个人是否具有获得自我、确立自我、显现自我的主体意识,如果没有这种主体意识与相应的努力,自我的消失与泯灭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幸,这恰巧是芸芸众生的常态。《寻找自我》中有这样寓意深长的一大段:
“经历很快烟消云散,我和于特经常谈起这些踪迹泯灭的人。忽有一天,他们走出虚无,只见衣饰闪几下光,便又复归沉寂。绝色佳人、美貌少年、轻浮的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便在世的时候,也不过像一缕蒸汽,绝不会凝结成型。于特给我举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所谓的‘海滩人’。此公在海滩上、在游泳池旁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在成千上万张暑假照片里的一角或背景里,总能看到他穿着游泳裤,混迹在欢乐的人群中,但是谁也叫不上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呆在那里,有朝一日,他从照片上消失了,同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不敢对于特明讲,我认为自己就是那种‘海滩人’。况且,即使我向他承认了,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曾一再强调,其实我们都是‘海滩人’,拿他的话来说,我们在沙滩上的脚印,只能保留几秒钟。
这是莫迪亚诺又深一层的寓意,也是他在小说里多次加以阐释的寓意:“也许我什么也不是,仅仅时强时弱的声波透过我的躯体,飘浮空间,渐渐凝聚,这便是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最终会烟消云散。或者,我们完全变成一层水汽,牢牢附在车窗玻璃上”。“他们几个人也渐渐丧失真实性,世间曾有过他们吗”。直到小说的最后,莫迪亚诺又用包含了这个寓意的一句话来结束全书:“我们的一生,不是跟孩子这种伤心一样,倏忽间在暝色中消失吗?”
多么充满了悲怆性的小说!其悲怆性足以与马尔罗哲理中被判处了死刑的人、加缪思想体系的西西弗相比,这是莫迪亚诺所力图描绘出来的又一幅人类状况的图景,在这图景中的寓意尽管不具有马尔罗哲理那种进取精神,也不像加缪的西西弗神话那样带有坚毅的色彩,而倒有几分茫然若失、悲凉虚幻的意味,但仍不失为一种醒世的寓意,它将有助于认识现代社会中种种导致自我泯灭、自我消失的现实,也将启迪那种打破“海滩人”存在状况的自觉要求与自为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也具有他吸引人的思想魅力。
莫迪亚诺于1968年以他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在文坛崭露头角,至七十年代末,又柑继以《夜巡》(1969年)、《魔圈》(1972年)、《凄凉别墅》(1975年)、《户口薄》《寻找自我》(1976年)这一系列颇有独特新意的作品,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1980年,他还只有三十三岁,正当年富力强,在整个八十年代里,他又做了些什么?他的创作有何发展?他的风格有何变化?他的离意有何充实?这些问题,不仅是文学史家、批评家、研究者所关注的,也是一般读者都感兴趣的。
《一度青春》(1981年)与《往事如烟》(1985年),就是莫迪亚诺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三五部作品中较为重要的两部。如果要谈它们的发展,那么,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莫迪亚诺式的题材与寓意的某种巧妙的变奏。
寻找、查询、探求,这是莫迪亚诺小说题材中常见的“基因”。在《星形广场》《夜巡》《魔圈》《寻找自我》中,不同的主人公或是在到处寻找自己的避难所,或是寻找自己的“母体”,或是寻找自己的血缘父亲,或是在寻找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历史、自已的“自我”。总之,他小说中的人物,就像漂泊的浮萍似的,都在寻求自己的根,自己的归依,自己的附着处,自已的支撑点。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存在于某种冷酷、阴暗、危机四伏的现实环境中,置身于某种异己的、带有敌意与邪恶意味的群体或社会团伙之中,因此,恐慌感与危机感,摆脱意识与追求意识,也就构成了这些人物存在状态的精神层面,他们的寻找与查询,正是他们的存在感与存在意识所促成的生存行为。
在八十年代的这两部小说里,作者似乎也在继续着查询寻找自我的这一主题。在《往事如烟》中,主人公从美国回到离别了二十年的巴黎,他情不自禁、不知不觉就一步一步进入了查询与寻找的状态,他要查询与寻找的,是他青年时期一段特殊生活中至今尚未完全消失的故人与一切残存的东西,是他那段生活的痕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莫迪亚诺小说中常有的那种现代的查找方式、追溯方式:找电话号码,通话进行探询,寻访有关的人与有关的地址、故里,查阅档案文件,等等……在《一度青春》中,主人公并没有追溯过去的要求,他二十岁时那一段奇特的、混合着辛酸与污泥的生活,是由作者从旁替他寻找出来、替他和盘托出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莫迪亚诺小说中常有的那种探找性的细节,生人公提着装有巨款的行囊过了海关,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寻找接头人……不论这些情节带有多大程度的“寻求”性质,莫迪亚诺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寻求探找,已经不再是人物生存中至关紧要的事,其前途命运、自我价值、存在意义息息相关的事了,不再是人物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怀着最急切的愿望非要完成不可的事了,它们只不过是一件可为亦可不为的事,它们在人物的生活中只具有一种追昔怀旧的意义。于是,我们就从莫迪亚诺八十年代的小说里,看到了他原有的那种“寻求”寓意的隐退,人物不再是寻根、寻源、寻找栖息地、寻找支撑点、寻找真实自我、自我价值的形像了,他们身上不再有追求意识,他们身上只有回忆的本能。`
在莫迪亚诺的小说、包括他八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还有一种共同的“基因”,那便是人物的本源、人物的历史与往事、人物的生活陈迹。它们在小说中往往是若隐若现、朦朦胧胧、含混不清,难以捉摸,因此,莫迪亚诺的小说往往也就是对埋藏在时间厚土下的生活、经历、往事的追溯与挖掘。当人物具有上述那种强烈的寻找意识与追求意识的时候,这种对过去的迫溯与挖掘,就成为了作者埋藏“寻求”寓意的所在。到八十年代,原来的那种对过去的“寻找”寓意没有了,作为一个一贯力求在自己作品里表达某种寓意的作家,莫迪亚诺还能在原有的“基因”中表达什么寓意?
尽管人物不再作那种牵肠挂肚的寻我与追求,但毕竟他现时的生活与历史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现时的自我与历史的自我之间存在着相当的反差,于是,这就成了八十年代莫迪亚诺寓意的落脚点。
在《一度青春》中,莫迪亚诺从男女主人公三十岁的现时,从他们自足安适生活的现状,回溯到他们二十岁时那一段贫穷、困顿的岁月,展示出他过去所处的那个发散出诡秘、犯罪气息的社会圈子、人群团伙以及他们当时冒险、屈辱、几乎像恶梦一样的生存状况的真相。在《往事如烟》里,在英国成了名作家的主人公,回到阔别了二十年的巴黎,旧地重游,点点滴滴都勾起了他对二十多岁时在巴黎那一段浑浑噩噩的岁月的回忆,在这回忆中,他过去所处的那个典型的巴黎式的腐化、堕落、花天酒地、颓废无聊、空虚迷乱的社会圈子又历历在目。如果说,七十年代莫迪亚诺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在现时潜在危险的压力下,在目前巨大的恐惧感与危机意识中,或者是在当前茫然失措的状态下,迫切地去寻找自己的仿史与过去,就像寻找一块避难的绿洲,那么,八十年代这两部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在现时安稳轻松的状志中、在当前心满意足的心境里,不得已地回顾自己本想忘得一干二净的厉史与过去,对过去那段生活唯恐避之不及就像躲避瘟疫。这样,在莫迪亚诺后来这两部小说里、现时与历史的反差,也就突出了一种现在“如释重负”的基调,一种“俱往矣”的基调。
“俱往矣”,这是古今中外一个经常唤起文学灵感的“意思”。这种感受、这种情怀、这种慨叹,曾是文学史上好些名篇佳句的产婆,也是这些作品藉以感人与传世的内在精粹。在外国文学中,华盛顿·欧文那篇闻名遐迩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可谓一典型的代表作,在小说里,瑞普一觉醒来,世上已过了二十年,俱往矣,时代变了,“朝代”也换了,就连酒店招牌上原来画的手执王笏的英主乔治,也成了手举宝剑、头徽三角帽的华盛顿将军。在中国文学里,这种“俱往矣”的情怀更留下了那么多俯拾即是的佳句华章,如卢照邻的“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淮见青松在”(《长安古意》)。陈子昂的“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燕昭王》)。刘禹锡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辛弃疾的“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满江红》)。苏轼的“百年兴衰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法惠寺横翠阁》)。柳永的“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在前朝”(《少年游》)。王勃的`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等等,等等。一般说来,这种“俱往矣”的主题,大多是对物换星移、世事沧桑的历史感慨与悲凉凭吊,另有一部分则是南柯一梦、往事如烟的个人追怀,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与范成大的“一枕清风梦绿萝,人间随处是南柯”,就是两例。
莫迪亚诺的这两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情怀,就属于“俱往矣”这一人类永恒的感慨,而且近乎“十年一觉”、“南柯一梦”的人生感慨,不过,在这里,不是美梦的消失,更多的是恶梦的消失,是主人公所经历过的一种现实、所交往过的一伙人的消失,这一伙人在巴黎曾经风光一时,喧嚣一时,纵情享乐一时,放浪形骸一时,而今安在哉?树倒猢狲散,他们都像幽灵一样消失了,像萤火虫一样陨灭了。在这个意义上,莫迪亚诺八十年代这两部代表作,是对巴黎红尘的点破,是对巴黎浮华的挽歌与凭吊。
莫迪亚诺这两部小说,还有较深一层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寓意,这寓意是他在作品中更有意识、更为着力地加以表现的。他不止一次有意让读者感受到人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这种悲怆性、渺小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社会现实的。在《一度青春》中,人在肮脏泥沼一样的社会环境中受到诸如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等冷酷无情、尴尬难堪的束缚与挤压,其存在意义荡然无存,人的存在沦落到了极为悲惨可怜的境况。小说中那个早年成名的音乐家拜吕纳,就是在无形的看似宽松的社会罗网中被窒息得每况愈下,沦为一个跑街,由此逐渐丧失起码的承受现实生活负担的能力,最后终于自杀。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二十岁年华的一度青春,都是极为卑践的、人的价值全部沦丧的青春。路易从军队里出来后,为了有一口饭吃,就像哈叭狗一样跟在不清不白的人后面,听从经济犯罪集团的调遣,在污泥里打滚儿而不愿自拨;奥迪尔在生存奋斗中为了能灌唱片、当歌星、有出头之日,宁可出卖自己的肉体,她在制片商人面前听从吩咐摆姿势任对方玩弄的一场,是小说中对人格沦丧富有怜悯之情的描写。在《往事如烟》中,一伙人过着行尸走肉的生活,完全无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可言,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与其说是由每个人的道德精神条件所决定,不如说是巴黎那种特殊社会活像魔法一样的粘性与惯性所决定的,这种粘性使这伙人像着了魔一样胶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魔力磁场,谁也无法摆脱这个磁场,超越这个魔圈;而特殊社会生活的惯性,则使得这一伙人像紧粘在一起的一个大雪团,沿着行尸走肉的下坡轨道而加速滚动,逐渐达到疯狂、精神崩溃的程度。
莫迪亚诺小说中人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形而上的。在这两部作品里,不论是路易斯与奥迪尔还是让·德克尔,都终于毅然爬出了他们原来巴黎生活的泥沼,摆脱了那个具有魔力的磁场,然而,他们的改弦更张、从新生活,并没有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一度青春》中的路易与奥迪尔拐走了经济犯罪集团的巨款,隐居在山区,买下了一幢木屋,办起儿童膳宿公离,生男育女,过起平静富足的小日子,在自己温馨家庭的小夭地里自得其乐。十五年过去了,当他们三十五岁生日来临时,他们对自己的一生别无他求,只愿不要再“从零开始”,只愿能眼见儿女长成大人后离开老年的父母。在这里,人全部的存在归结为平庸苟安的人生,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缩小到了这样一种可怜的地步,而且,若干年后,他们也会像过去千千万万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一些年,而后就像幽灵一样消失的芸芸众生一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的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是命定的。
《往事如烟》的让·德克尔的存在,显然要比路易与奥迪尔要高两个层次,活得比他们有意思得多,他从巴黎走到英国,从事写作,成了一个在不少国家都拥有读者的侦探小说家,当然,丰厚的收入、美貌的妻子、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儿女、豪华的别墅,他都应有尽有。然而,当他回到巴黎,亲眼看到了原来那些同伙都一个个消失,一个个成了幽灵、幻影,“就像所有的黄萤和萤火虫”,对此,谁也不会怀疑他自已也是“所有的黄萤和萤火虫”中的一只。在这里,可以又一次着到人的存在的悲怆性与渺小性。莫迪亚诺不仅让读者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把对这种悲怆性与渺小性的明确感知,赋予他的人物。《一度青春》中的路易就“感到在林荫大道的灰尘中,自已不过是一粒尘埃,然而,这在空气中华竟是一种存在”。同样,在《往事如烟》中,正是让·德克尔也明确把世人比喻为生生死死的萤火虫。
这个主题、这个寓意,我们也似曾相识,它在莫迪亚诺的小说中,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在他六、七十年代钓小说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把人的存在视为水气、尘粒、幻影的窝意,就已经看到了他关于“海滩人”的哲理。海滩照的背景中有一大堆人,其中的一个人影他是谁?他在世界上做过什么?他是否还存在?对于这个世界来说,这个海滩人只不过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一张曾经显露过的面孔,一个曾经出现过的影子,一只曾经闪烁一瞬的萤火虫。
莫迪亚诺的寓意使人想起十七世纪大思想家巴斯喀早已描迷过的人的状况的图景:“请设想一下,戴着锁链的一大排人,他们每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每天,其中的一些人眼看着另一些人被处死,留下来的人,从他们同类的状况看到了自己的状况,痛苦而绝望地对视着……这就是人的状况的图景。”在接触到了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上,莫迪亚诺又使我们想到二十世纪的大哲人马尔罗、萨特与加缪,所不同的是,莫迪亚诺没有这些哲人所提倡的人面对着命定的、悲剧性的状况要有所为的哲学,他没有马尔罗那种反抗人的状况与命运的超越哲学,没有加缪那种面对荒诞仍追求存在价值的哲学,也没有萨特那种在荒诞的状况中顽强奔突的自我选择的哲学。莫迪亚诺仅仅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描述人存在的命定性、渺小性、短暂性、悲怆性。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局限。
在九十年代,莫迪亚诺是否还会开拓他的文学领域,是否还会发展他原来作品中的一些寓意哲理,如果他不会再有重大的开拓与发展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说,莫迪亚诺这一条水流几乎可清澈见底了。
——原题:“莫狄亚诺的魅力——《寻我记》《魔圈》《夜巡》及其他”“莫狄亚诺在80年代的变奏——《一度青春》《往事如烟》《凄凉别墅》”,曾发表于《当代外国文学》1991年2期、1993年2期,收入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一书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