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大的事情,也不过是忽生忽灭的水泡,留不下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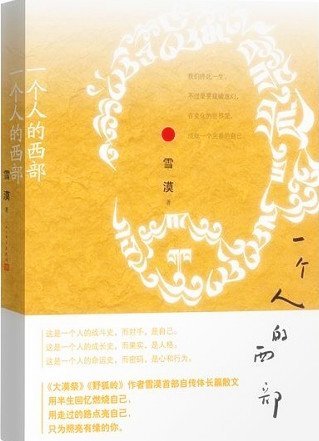
《一个人的西部》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
死亡夺走了二弟
1992年的一天,二弟陈开禄来找我。他说肋下长了个硬疙瘩。我一摸,果然,便问他疼不疼,他说不疼。我说,也许是个脓包吧。他就到医院开了逍遥丸,吃了好几天,可一直不见好,还越来越大了,而且长得飞快。陈开禄有些发慌,又来找我。我安慰他说,不要紧,坏东西哪能长那么快,但还是带他到医院做了B超。结果出来后,医生说是肝包虫,开刀把虫子取出来就没事了,但从手术室里出来后,肝包虫却变成了晚期肝癌。那消息,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我一下就懵了。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二十六岁的弟弟,竟得了那种好不了的病。我突然有了一种噩梦般的觉受。瘫软像潮水一样涌向了我,我想,妈妈知道了咋办?那一刻,我特别希望一切都是一场梦。要是一场梦,该多好?
医院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来往的人,也像是飘来飘去的影子。那段日子里,我看不到太阳。世界变成了一部灰白电影,我是穿梭在电影里的幽灵。所有的声音,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变得沉默了。人前,我总是挤出笑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人后,我总是流泪。弟弟的病像是心头的刺,时不时地,就会在我心里扎出血来。
那时,我便祈求观音菩萨,希望她能改变弟弟的命运。假如菩萨真能显灵,救了我弟弟,我愿出家为僧。但奇迹没有出现。不过,我仍然每天禅修,并没有怀疑自己的信仰。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可能怀疑自己的信仰,都会问,到底有没有佛菩萨?但我不是这样,之所以我不会这样,是因为我不是为了求神庇佑而走入信仰的,我是真的向往佛教的智慧和慈悲,真的想要升华自己,所以,就算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就算我失去了一切,也依然不会动摇我的信仰。信仰像是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我的心头,不管心潮如何澎湃,它仍是坚定不移地立在那里。那时节,因为弟弟的死而陷入了半痴呆状态的我,仍然能感觉到它望着我的双眼。我仍然坚持着每天的修行、读书、写作。
弟弟住院时,我为他包办了很多的事情。最初,我没把弟弟的真实病情告诉任何人,始终一个人承受着痛苦,没人可以倾诉,也没人可以依靠。有时,我甚至希望,弟弟能快些结束这苦难的人生。那实实在在的生命,在我眼中,也变成了一捅就破的肥皂泡。这给了我很大的打击。
弟弟确诊后的几个月里,我没去教委上班,一直陪着他。陪重病病人是世上最累的活儿,我总是替他挨痛,总是希望自己的挨,能真实地减轻他的疼。有时,只陪一个小时,我就累成泥了。后来,我,二舅畅国权,妹夫齐加平三个人轮流陪,每人一小时。那时,他们都知道弟弟得啥病了。
虽然我们都希望弟弟的病好,但他腹部的那个大球,仍在吹气似的长。
我们都在等那个非来不可的东西。
弟弟睡觉时,我就坐在旁边读书。有时,思绪会像水一样流过。我想起好些小时候的事,想起我们俩一起走过的日子,想起他带着面粉来学校里看我,想起他憨憨的笑,想起他被人骂了之后通红的脸……我真的不敢相信,那个陪我走了二十六年的人,竟然很快就要从世上消失了。但是,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身体,看着他鼓起的腹部,看着他黄瘦的脸颊,我又不得不相信:我年轻的弟弟,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死亡。
弟弟这辈子,真的没有活好。他初中毕业就去卖苦力,供我读书,到死都是农民工。但有一次,我却伤害了他。当时,我们正在斗嘴,气头上的我冲口而出:“你不过是个卖苦力的!”他顿时怔住了,半晌后号啕大哭。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他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农民身份,为这,他一直很自卑,觉得自己比城市人矮了一截,但他没有想到,连哥哥也瞧不起他。
其实,我从来没有瞧不起他。对他,我有很深的感情,也很感恩。我明白,我能读书,也因为他的付出,可一时冲动,竟说了不该说的话。那是我唯一一次伤害他。我当时就后悔了,却无法改变发生了的事情,也不知如何向他忏悔,怎么说,都好像会越描越黑。我想任时间冲去那记忆,可那画面,却成了插在我心上的刀子,而弟弟的死亡,又让我失去了忏悔的机会。他死后的许多个夜里,我都会从睡梦中哭醒,在孤独的空气中大叫着:“弟弟,宽恕我吧!”但漆黑中没有回音。
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时,我的生命里,就没了好多执着。我目睹了一个健壮的生命逐渐衰竭、消失的全过程——他1992年11月查出癌症,12月15日已走进了黄土堆,生命的消逝,竟那样快——名利啥的,真成过眼云烟了。
我整个人进入了一种半痴呆的状态,人问啥,我都不知道,反应不过来。好多人就说,陈开红傻掉了。虽然我还是坚持读书、修行,但写不出任何东西。写作基本上中断了。
像《大漠祭》中写的那样,每次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弟弟的化身,总会像鲁迅小说《药》里的老女人那样,对它说话。当时,我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我总会梦到弟弟。梦里的弟弟是活着的,却阴着脸不跟我说话。阴着脸也好,活着就好,可一段时间之后,连阴着脸的弟弟,我也梦不到了。我再次陷入了一片黑暗和绝望。
家里的情况也非常糟糕,钱花光了,母亲也病倒了。她的大便里有血。我马上陪她去医院做检查,生怕她得直肠癌。幸好,检查了很多次,医生们都说,她只是得了痢疾。但我的心里,仍像揣了块石头般地沉重。
三弟陈开青也突然从新疆回来了。回来的他,舌头上裂开了好多血口子,非常吓人。我想,刚死了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咋也变成这样了?便带着他到处看医生。医生们都说不要紧,他慢慢调养着,也痊愈了,就给我讲了好多故事。
原来,开禄去世时,开青正在几千公里外新疆的森林里伐木——他不知道陈开禄病危的消息,我们没法通知他——那时是严冬,风雪交加,他和同伴在齐腰深的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差点冻死,后来,他们在一个山洞里躲了好久,才被几个哈萨克人救下。他说的故事我都记下了,想写进小说里,但一直没用上。
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都让我深深地感到了无常。虽然我一直把生死作为参照系,来做每一个决定,但真正遇到至亲死亡时,那种巨大的冲击感,还是不一样的。那时节,我才终于明白了什么叫经历死亡。那时的觉受,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它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我直观地感到,当一个人走向死亡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包括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他的肉体,等等,陪着他的,只有自己的灵魂。这成了我后来走向觉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
对死亡的感悟,让我放下了生命里的很多东西。那段时间里发生的很多事,对我来说都没了实体,都像是水泡般忽生忽灭,除了家人的健康,我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了。唯一鲜活的,就是弟弟的死。
1992年3月到12月,一共九个月间,我读书三百六十六个小时,写作二百一十七个小时,平均每天写作不到一个小时,那段时间,真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绝境了。但是我仍然不想放弃。虽然弟弟的事告一段落后,我又开始写作,但仍然写不出能让自己满意的东西,生命于是变成了一种煎熬。我只能将几乎所有的生命用于禅修。
过了两年多,我才真正缓过来。缓过来之后,我就把弟弟的事写进了《大漠祭》。从《大漠祭》中,你可以看到弟弟从生病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和家人的心灵历程。或许,你会看出一种感悟来;或许,你会更懂得珍惜生命,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让自己觉得没白活的事情。
因为,虽然很多事都值得做,很多享受也很好,但每个人的生命空间都非常有限,生命时间也很有限,而人的一生里,能留下意义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好些人活了一辈子,有过辉煌,有过潇洒,有过得意,但到头来,对别人产生不了任何价值,也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哪怕非常优秀,也只是茫茫人海中的水滴,被岁月的艳阳一照,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活着,只是对生命的消耗,有啥意义?可好多人,一辈子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比如那些给陈开禄动手术的医生们。
记得,那些医生们也在私底下议论着,说弟弟得了实质性的病——就是说,他们已知道那病的真相,却仍然告诉我们,那只是肝包虫——而且,凭当时的医疗水平和弟弟的症状,他们也不该误诊的,可他们偏偏叫弟弟去动那个毫无意义的手术,为啥?为了手术费。麻醉师没给弟弟打麻药,就让医生在弟弟的肚子上割了一道五寸长的口子,为啥?因为我们没给麻醉师送礼——我一直不敢想象,那锋利的屠刀,是如何伸向苦命的弟弟。
我在《大漠祭》后记中写了我的希望,希望那些医生和偶尔有点权力的人们,能早些发现世间利益的无常,建立一种岁月毁不去的德行,为世界贡献一点美好。
要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无论利益、享受、地位,还是别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天大的事情,也不过是忽生忽灭的水泡,留不下什么。生命也是这样。无数个陈开禄来了,又走了,他们迷恋过的一切,他们放不下的一切,都消失了。真正伴随了他们的,只有灵魂深处的疼痛和寻觅。
我们兄弟三人用颜色起名字,陈开禄本名开绿,后改名开禄,是因为他希望能吃上官粮,能月月混个麦儿黄。但他奋斗至死,都没有摆脱农民的身份。可是,假如摆脱了,又能怎么样?当农民的陈开禄也罢,吃上官粮的陈开禄也罢,最终的归宿都是死亡。他在世间的身份,并不能减少他患癌时承受的痛苦,也不能改变他的命运,财富和地位到头来,都会变成别人的东西。你的一切——包括你的老婆孩子,甚至包括你百般爱护的身体——最终都不属于你,你还能真正拥有啥?你辛苦了一辈子,错过了很多追求梦想的时间,又是为了啥?
前边说过,《猎原》中张五的生活原型是我的伯伯陈召年。他晚年得了癌症,没钱治病,也买不起止痛药,只好躺在家里,疼得像牛一样号叫。他没有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尊严,挣扎着活在地狱里,只是为了最后的死去。后来,我带了几支杜冷丁——杜冷丁不好找,我是给弟弟准备的,但那几支杜冷丁还没用完,弟弟已死去了——和一块鸦片去看他。他看到鸦片,双眼立刻放出了异样的光彩,然后,用火钳烫了点鸦片,贪婪地吸那白烟。那细节,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后来,我就用《猎原》定格了那个瞬间——我想告诉这个冷漠的世界,有些人活得非常艰难,他们很需要别人的关怀和帮助,可愿意关注他们的人,又有多少?这个喧嚣、麻木的世界,能感觉到一种疼痛吗?
我想为无数的张五说些该说的话。
——刊于《中华文学选刊》2016年第一期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