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好多人道主义的作品诚然写得非常拙劣,但在宗教文化业已衰颓的今日,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容我们加以轻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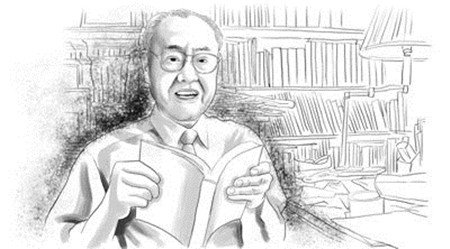
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
1952年开始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时,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算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二十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鲁斯德、托玛斯曼、乔哀思、福克纳等--我都已每人读过一些,再读五四时期的小说,实在觉得他们大半写得太浅露了。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他们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了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了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
所以我在本书第一章上里就开门见山,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便从事于道德问题之探讨(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当今批评家史坦纳(George Steiner)曾言,西洋文学三大黄金时代当推普理克理斯(Pericles)执政雅典期间的古希腊悲剧时代;英国的莎翁时代;以托尔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二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
索福克理斯、莎士比亚、托杜二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杜二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
索、莎、托、杜诸翁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生之谜到头来还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事实上,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作家都具有这种宗教感的。我既是西洋文学研究者,在“结论”这一章里就直言“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这句话,不少朋友(我记得侯健、白先勇都当面对我说过)认为是一针见血之论,逗人深思。
在当时我对传统中国文学认识不深,但身为中国人,总觉得这个传统是极为伟大的。在密歇根大学教了一年中国思想史,佛学、理学虽对我并无多大吸引力,总认为自己慧根太浅,也总相信,凭其深厚的宗教、哲学背景,中国传统文学应同西方文学一样,对人生之谜作了极深入的探索。所以我在“结论”里也老实不客气认为现代中国人“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写出来的小说也显得浅显而不能抓住人生道德问题的微妙之处了。
我写完本书后,即在匹次堡大学、哥大教起中国文学来,传统文学十多年来真的读了不少。1968年我还写出了一本《中国古典小说》专论,自己对传统小说、戏剧真作了些研究。我渐渐发觉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之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了多少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诗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那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来。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诗篇里所表扬的不仅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义的精神。
再反顾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说,大半传统小说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视人生的写实性,也为其宗教思想所牵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当然,《红楼梦》自有其比较脱俗的宗教思想,但其倾向则为逃避人生,并非正视人生。贾宝玉面临的苦恼太多了,最后一走了之,既对不住已死的黛玉、晴雯,更对不住活着的宝钗、袭人。比起《卡拉马助夫兄弟们》里的阿利屋夏(Alyosha)、《复活》里的南克鲁道夫(Nekhludoff)来,到最后贾宝玉只能算是自归灭绝的懦夫。他的情形同《白痴》密希根亲王(Prince Myshkin)也有些不同。密希根亲王最后真的转成白痴,但假如他一旦理智恢复,他还要努力拯救他所爱的人们的。
我多年读书的结论是: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但同时我也不得不同意胡适的一句话:我国固有文化的一个最大特色,即是我们的先民,“他们的宗教比较的是最简单的、最近人情的”。佛教输入之后,历代读书人不像一般愚夫愚妇这样的深受其骗,其宗教信仰“比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请参阅《三论信心与反省》,《胡适文存》第四集。)
目今西方社会已跨进了脱离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阶段,大家信赖科学,上教堂做礼拜,对大半人来说,只是积习难改。这个习惯在美国很可能会维持100年,但二次大战以还,英国人、北欧人就很少进教堂去做礼拜了。天堂、地狱早已没有人相信了。曾在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各种艺术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伟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样子不可能在下一世纪再有什么光辉的表现了。当然,耶稣爱世人的精神仍会延续下去,但本质上同世俗的人道主义已将没有多少区别了。
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也比不过仍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洋文学。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也越来越薄弱了,他们日后创作的文学将是个什么样子很难预测,但无论如何,莎翁时代、十九世纪西方小说的黄金时代将是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情形恰相反。我们的先民宗教信仰极简单,而后世的读书人宗教信仰也较薄弱,大半可说不信什么神佛──假如凭这个假定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二十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古代读书人,受了孔孟教育,讲道理个个都应该甘为人民喉舌,揭露朝廷、社会上所见到的黑暗现象。但他们生活在皇帝专制政体下,大半变得“明哲保身”、“温柔敦厚”起来;也有很多人,无意官场,或者官场失意,人变得消极,求个“怡然自得”就够了。到了晚清末年,专制政体即将瓦解,读书人才真敢放胆写出他们心里要说的话来:所谓“谴责小说”的盛行,不是没有理由的。
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无论如何,自从小女孩普遍缠足以来,这个中国传统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缠足妇女,四肢得不到适当运动,生不下孩子惨死的,一千年来要有多少?姜贵最近在《〈曲巷幽幽〉后记》里讲起了缠足:
一个陋习的逐渐形成不足异,足异的是明明致人于残废的肢体毁伤,须历千年之久,始因外力的侵入而渐觉其陋,渐悟其非。又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奋斗,奔走呼号,无可奈何,这才被革除。最早,无人防微杜渐。既经形成,无人敢非其非。其难如此,炎黄子孙的智慧和勇气到底哪里去了?
姜贵自己是“五四、三十年代小说传统”的集大成者,他那句责问也写出了当时作家面对黑暗的现实,心里所藏不住的愤慨。台湾有些批评家,拾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唾余,喜在“人道主义”上面加“廉价的”这三个字。我总觉得同情心、爱心是人类最高贵的情操;好多人道主义的作品诚然写得非常拙劣,但在宗教文化业已衰颓的今日,人道主义的精神是不容我们加以轻视的。
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但现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义的西方名著尺度来衡量现代中国文学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变了质,今日的西方文艺也说不上有什么“伟大”。
但在深受西方影响的全世界自由地区内,人民生活的确已改善不少,社会制度也比较合理;假如大多数人生活幸福,而大艺术家因之难产,我觉得这并没有多少遗憾。但丁的诗篇诚然是西方文化的瑰宝,但假如十三世纪的义大利人民能逃出中世纪的黑暗,过着比较合理、开明的生活,但丁活在那个环境里,庸庸碌碌过了一生(能同皮阿屈丽丝结婚当然更好),即使一无写诗的灵感,我想他也是心甘情愿的。
总括一句说,本书1961年出版后,中国新旧文学读得越多,我自己也越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越来越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时到今天,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说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当然任何国家的文字、语言不断在变,今日的诗人、剧作家,仅论辞藻的丰美,当然绝对比不过杜甫、关汉卿,正像今日英国诗人、剧作家比不过莎士比亚一样。但六七十年来,善用白话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数不能算少;近20年来那几位突出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他们的白话文,比起五四时代的那批名作家来,更是耐读、精炼得多;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写,白话文的前途是不容我们去忧虑的。
我对中国新文学看法之改变,在本书三篇附录里即能看出些头绪来。在近文《人的文学》里,我采用这个新观点来审视胡适、周作人二人的成就,更强调他们不断“在古书堆里追寻可以和自己‘认同’的思想家、文学家”,以便建立中国文化“真传统”这番功不可没的努力。如把“文学革命”这一章同《人的文学》对读,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
但我虽更珍视新文学这个传统,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语见《小说史》初版原序),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一般说来,新文学作家比古代文人更正视现实,关怀民间疾苦,但他们发表作品太容易了,其中天分不高、写作态度马虎的,人数也多的是。
本书写作期间,我尽可能浏览了长短篇小说单行本,同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和长篇连载,借以选定那几位小说家值得专章处理。我对那些入选的作家则作了更深一层的研究,尽可能审读他们全部的作品。这样写书当然要比写流水账式的文学史费力得多了。要决定那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就不太容易。三十年代初期,左翼名小说家要有多少,我特别看上张天翼、吴组缃,表示我读了好多齐名的作家后,认为这两位的艺术成就最高。
久享盛名的茅盾、老舍当然是一定入选的,但其个别作品之优劣还非得重加估断不可。《子夜》一直被评家称为是茅盾最伟大的杰作,我偏认为它比不上他早期《蚀》、《虹》和后期《霜叶红似二月花》这三部长篇。《猫城记》这部小说,老舍自己认为写得不好,当时评价也不高,我偏要加以重视。三十年代丁玲的声望,仅次于茅盾、老舍、巴金诸人,我审读她那时的作品,实在一篇也说不上是佳作。评审四十年代的作家,现成的参考资料更少,非得郑重加以抉择不可。本书讨论的两位四十年代作家──张爱玲、钱锺书──我很高兴到今天在美国年轻一代从事新文学研究的学人之间,也变成了大家必读的热门作家了。
但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我当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来,实在少得可怜。(别的图书馆收藏的也不多,但我如能去史丹福的胡佛图书馆走一遭,供我参阅的资料当然可以多不少。)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有系统地读了萧红的作品,真认为我书里未把《生死场》《呼兰河传》加以评论,实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
1978年11月28日,纽约
摘自《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