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白鹿原》沿袭了文学传统中关于土地与家族的叙述,把家族故事以“史诗性”的期待,带入了九十年代的文学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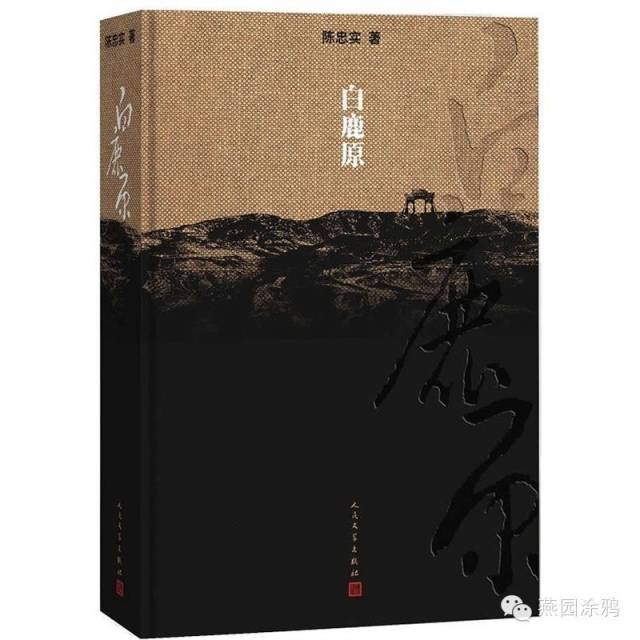
陈忠实与违心修改 又再度复原的《白鹿原》
费孝通把中国称为“乡土中国”。是的,在这个农业国家,每个人都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乡土精神和审美理想,都形成一种独特的“乡村文本”。它自身与生俱来的宏大、沉寂、稳定的叙述,既规范和限制作家的叙述,又对他们的想象、叙述、诗情产生深刻影响。
九十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陈忠实获得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与张炜时运不济的《古船》相比,呈现出不同的意味。
《白鹿原》沿袭了文学传统中关于土地与家族的叙述,把家族故事以“史诗性”的期待,带入了九十年代的文学星空。
《白鹿原》在一个宏大历史背景下,写了白鹿两姓一族三个家庭的恩恩怨怨和纠葛矛盾,以及家族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展示了“一部民族秘史”。小说没有直接写阶级对立和矛盾,而更关注历史斗争背后的文化行为。叙事的焦点始终对准聚族而居的白鹿原,通过白、鹿两姓合二为一的宗法文化的恒长与震荡,探索民族的生存和精神历程。
陈忠实自己说,是的,“我要全面地反映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有它腐朽的一面,还有很伟大的一面,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不能延续下来。”为此,作家精心塑造了一个大儒朱先生形象。可惜作品中的朱先生,因为过多地负载了作家的理念,使之成了超凡入圣、不食人间烟火的现代大儒。儒家文化,也成了中国文化复兴的灵丹妙药。既违背了历史,又与《白鹿原》的浓重写实的艺术风格相悖,此乃一大败笔。
但《白鹿原》苍凉的雄浑的叙事,以及刻画塑造了白嘉轩等一个个真实血肉丰满的人物,仍不失为一部永恒的民族史诗。
八十年代初,我与陈忠实相识。那时,他已经创作了表现陕西关中农民生活的《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信任》《初夏》等中短篇小说,并获多种文学大奖。初次在《当代》编辑部相见,他那如黄土高原有着纵横交错沟壑的脸上,凝铸着岁月的沧桑,很像一个关中农民,文如其人,怪不得他的小说如土地般浑厚却粗糙。其实,忠实是个地道的文化人,父亲是农民,却珍藏一大箱书籍,十分重视文化。
忠实刚上初中时,不管风雨冰雪,父亲都会骑自行车驮着一口袋馍给儿子送到离家很远的学校。读过木箱里的书,到初二时,就对文学发生兴趣,开始动笔写小说。一九六二年,从西安市三十四中毕业后,在西安郊区当中小学教师,并自修大学。三年后发表小说处女作《夜过流洪沟》。
一九八四年夏,我与忠实和王朔等作家,到京郊游览幕田峪长城。我们谈到了古华的《芙蓉镇》。忠实很赞赏古华透过小社会的变化来概括大社会、大时代的变迁的笔法。忠实说,《芙蓉镇》是反思历史的,其反思集中在极左的阶级斗争对人的戕害。它的最大的功绩是坚持“写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发现,忠实在反思着自己的创作实践。说实话,忠实的小说创作,始终没有彻底摆脱政治为文学创作搭建的樊篱,尽管他的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但写不出活的人物,缺乏丰盈的色彩和灵动之气。在我的心里,朴实而忠厚的忠实,能发表不少色调单一的作品,已委实不易,再往下走,实在艰难。我不能直接向忠实表达我这种悲观,只是以劝他多读书,暗示他已江郎才尽。然后将话题转向脚下残破悲凉的幕田峪长城。
自这次晤面之后,忠实似默然退出文坛,作品不多。
大约是一九九二年初春,隐退了五年之后的忠实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部长篇已经脱稿,希望《当代》派人去取,那口气依如往昔的他,谦卑而亲切。于是出版社派了两位编辑去西安。我当时心想,那个朴实得如同黄土高原的忠实,怕会交来像黄土高原一样朴实的作品吧,并未寄以厚望。
时至今日,我还未能忘记,两位资深编辑向我们陈述取回《白鹿原》稿件的情景:他们到西安后,陈忠实极热情地带他们看大雁塔、兵马 俑,并不提长篇小说。直到他们登上返京的列车,忠实用那双粗壮裹着青筋的手将一摞盈尺的书稿交给他们,那眼神闪着灼人的光亮,似乎在说:“我连同生命一并交给你们了!”他们被忠实的眼神所感动,躺在卧铺上,分头阅读起来,这一上手竟再没放下。
回到北京,立刻组织人审读,几天以后,煞红了眼睛的审读者,聚到一起,几乎同时惊呼:“陈忠实写了一部大作品!”
读完《白鹿原》,我突然发现,一个陌生的大智若愚的陈忠实站到了面前。《白鹿原》时空对立,静动、稳乱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纠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艺术魅力,且把人在历史生活中偶然与必然的复杂关系,揭示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竟然是出自有些“木讷”的忠实之手,我惊愕了。忠实何时得“道”成“仙”,看透了文学的奥妙?而我的眼拙,让我羞愧难当。
一九九三年《当代》分两期刊出《白鹿原》后,陕西轰动,北京轰动,整个文坛轰动。其实,陕西一位有影响的评论家,在读完《白鹿原》初稿,就激动得跳将起来,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那评价令忠实害怕,我们问了半天,忠实才保留了评论家的一句话:“真真咥了个大活!”至今,这句韵味十足的陕西土话,还铮铮地响在黄土高原。
继西安之后,《白鹿原》又在京召开了作品研讨会。时逢仲夏,天气晴好,位于西刹海西侧作协的文采阁,热闹非凡。全国知名的评论家如雷达、西来、振邦诸兄一一与守在门口的忠实握手入阁。忠实憨憨地笑着。我拍拍他宽厚的肩头,使劲地握着他湿热的大手。
五年不通音讯,再见到他时,脸上皱纹更密、更深,双鬓染霜,头发稀疏花白,但宽额下那双熟悉的眼睛依然闪烁着如同黄土高原般的深邃和柔静。沉静是一种生命境界,沉静又是文学的高境界。
研讨会由陕西省宣传部部长王巨才主持。会上评论家毫不吝啬赞美之辞,高度评价了《白鹿原》。有的评论家指出,《白鹿原》是个整体性的世界,自足的世界,饱满丰富的世界,更是一个观照我们民族灵魂的世界。它以凝重浑厚的风范跻身于我国当代杰出的长篇小说的行列。
有的评论家则称,《白鹿原》具有文化性、超越性和史诗性。有人把《白鹿原》与张炜的《古船》作了比较,认为同是一部政治文化色彩浓重的长篇,《古船》写的是人道,《白鹿原》写的是人格,它是通过家族史来展现民族灵魂史的。
也有评论家指出《白鹿原》有借鉴《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的经验,但功夫还不到家等缺陷。
研讨会颂歌是主旋律,也有驳杂、不协调的声音。我听得热血沸腾,忠实埋头记录,大汗淋漓。最后轮到忠实发言。五年的修炼,忠实已修炼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但他说到感谢评论家的关心爱护时,还是热泪盈眶,有些哽咽了。
陈忠实到四十五岁时,他想,如果到了“知天命”之年,还拿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也许后半生将伴着失落和孤独度日了。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无法回避的紧迫感。对生命的苍凉感和负债感、成就事业的人生抱负与生命苦短的焦灼和惆怅,是千百年中国文人对生命的双重体验的主题曲。
一九八七年,在长安县,陈忠实与一位文友秉烛夜谈时,他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如果五十岁还写不出一部死了可当枕头的书,这辈子算白活了!”就在这年农历正月十五闹花灯前,陈忠实辞去兼任的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职务,安排好年迈的老娘和不大的子女之后,便裹着一件棉大衣,在原上凛冽的寒风中,与妻子离开繁华大都市,一头扎进了白鹿原下自己的一座农村小院里。闭门谢客的他还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不接受采访;不参加无关宏旨的应酬和社会活动;不理会对他过去作品的评价。
在千古流淌的灞河畔,在黄土裸露的原下,开始对周围三县进行走访调查。过了“立春”又到“谷雨”,乍暖还寒,冷风刺骨的时节,他伴着如豆油灯,细心地从一摞摞卷帖浩繁的县志、党史等资料中,打捞宝贵史料。没白天黑夜地埋头抄录了三个月。
从浩瀚的史料中,他看到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中国历史巨大进程中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在白鹿原留下了生动、深刻的投影。其间霍乱、瘟疫、饥荒、匪祸也给农民带来深深灾难和斑斑血泪。翻着这一页页沉重的历史,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他心中,这块土地上生灵也全都动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沉浮,诉不尽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整个白鹿原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的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披着棉大衣或一身短衣裤的高大汉子,风里雨里、雪中雾中,或骑车或步行在白鹿原上上下下的乡、镇、村、堡上匆匆赶路。或见他蹲在村边地头,听那些穿着油渍麻花黑袄、头缠白羊肚儿手巾的农民讲故事传说。有时,他又端着大海碗,凑到农家汉子堆里,听他们唱着高亢的秦腔或拉家常。有时,他会在村头残破的碾盘上与人家下棋。凑巧赶上婚嫁、丧事,他会挤进人群,陪他们笑唱,陪他们落泪。他已习惯在黄土古道上踽踽独行,叩问历史或和他酝酿的人物对话。
每天,他黎明即起,冲上一杯酽茶,点上雪茄,在熹微的晨光雾气中,踱步在早已残破的有着枣树的小院。走啊走,待他重新进入小说的艺术氛围,召回和他相处多日熟悉的各种人物,便慢慢地转回身,进屋伏案疾书。
大约是太阳西斜,他会暂时告别他的人物,推开柴门,倒背着手,悠哉游哉地走进别的农舍和老乡拉家常,听白胡子老汉说古道今。人家留他喝胡辣汤,他也不客气地端起比脑袋大的海碗,与老汉走出家门,蹲在墙旮旯,与邻家一起大声喝着,看光着屁股的小孩子打闹。晚上,在灞河畔,看长天月色,听十里蛙声,然后爬上原坡,坐着数点点的灯火,望流萤明灭。有时,他会咿咿呀呀地唱起秦腔。秦腔高亢、粗犷又低沉婉约,那里面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人物,悲壮苍凉的曲调正与《白鹿原》的基调相谐。
无怪有的读者说:“看《白鹿原》,有听秦腔的感觉。”的确,正是秦腔,让《白鹿原》深入到秦汉文化的魂魄。同时,沉郁苍凉的秦腔也抒发了陈忠实的寂寞孤独的心境。让人蓦然想起当年的杜甫的诗句“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江汉》)。
后来,过去多年,我与忠实受邀,到西柏坡参加一次笔会,同住一室。在谈到《白鹿原》创作时,忠实说:“我躲在原上写《白鹿原》,既兴奋又寂寞。我体会到,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一九九一年底,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结结实实覆盖了白鹿原时,陈忠实推开小屋,走到院落里,扬起脸,任硕大晶莹的雪花砸在脸上,心里却油然升起些许的矛盾。熬了快五个春秋的《白鹿原》已经接近尾声了。他所钟爱的人物将与他渐行渐远了。两个叛逆者,白灵与兆海最终要出走了……
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羊年农历腊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陈忠实终于给《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前几天,陪他整整五年的妻子回西安时,他关照熬瘦了的妻子说:“咱们再见时,书稿肯定就写完了。你多买些炮,要雷子炮!”
忠实再到积着雪的小院,静得出奇。整个世界只有他和《白鹿原》中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的几个人物。刚才,文稿杀青,他将一大摞稿件码齐,然后点上一支雪茄,烟雾在眼前缭绕,不知怎的,两颗清泪慢慢涌出眼眶,正可用“独自掩卷默无声”来形容。
《当代》全文发表《白鹿原》后,整个文坛如一鼎沸锅。他却从灿烂重归于平静。五月,他约了几位好友,花生米就着啤酒,边谈边饮,平静而惬意。等到夕阳西下,他又悄没声息地再次告别西安,迎着麦香重返白鹿原下的那座小院。点上雪茄,斟上一杯西凤酒,然后唱起土味十足的秦腔。望着一轮明月,心境平静如水。
北京的研讨会开罢第二天,忠实应新华书店之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我陪他到书店。一开店门,外面已排起长长的队,几个小时,忠实忙着没抬一次头,比起一般冷清的签售,可谓盛况空前。
当晚,忠实在我社门口孔府酒家宴请我们和北京评论界朋友。美味佳肴,玉盘珍馐,再加上陈酿好酒,席上热闹非凡。酒过三巡,忠实的脸就红了,不再如先前那般拘谨,笑得灿烂且豪放。 忠实站起来,说:“我给朋友唱段秦腔。“
他唱的是《辕方斩子》中杨延昭一段唱:“见太娘跪倒地魂飞天外,吓得儿颤兢兢忙跪尘埃……”唱得声情并茂。
一九九九年冬,庆祝新世纪到来,中国作家们集结于四川成都,白桦、叶南、忠实、蔡其矫、李瑛、苏叔阳、邓友梅等诸友欢聚一堂。我与忠实爬峨眉、游乐山,夜间到街头吃夜宵,啤酒小炒,味美价廉。临别时,忠实挥毫为我写了“怡然”条幅。让我分享他宁静怡然心境。至今此条幅挂我书房,见字如见君也。
西柏坡笔会与忠实见面时,见他气色不好。他说常腰疼。我回家之后,托朋友给他带去一些中草药。每年全国两会时,作为政协委员的忠实来京开会,我有时去看望他。我给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走向诺贝尔丛书”时,选了《白鹿原》。给中国文史出版社主编“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时,为忠实编了一本《拥有一方绿荫》,还获了全国奖。
《白鹿原》横空出世,给一度沉寂的新时期文学带来了震撼与信心,它告诉中国作家,我们民族的文学思维并没有停滞,作为有社会良知的作家,也从未放弃对时代精神价值的严肃思考。但大气磅礴的《白鹿原》,却遭到过不公平待遇。
自打《白鹿原》在《当代》上发表,就不断听到来自上面有关领导一些若隐若现的指责、批评。而据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羊城晚报》转引《金陵晚报》的消息说,一个叫什么王某的领导人,批评《白鹿原》和《废都》一样,写作的着眼点不对,明确把《白鹿原》和《废都》两部小说“列为影视禁拍作品”。我们在北京听到上级领导在一次什么会上,也批评了《白鹿原》,并说不要再宣传《白鹿原》等话。直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在天津开评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优秀长篇小说时,一位临时主持人竟粗暴地不让提已获茅盾文学奖的《白鹿原》。
在当时,《白鹿原》在某些领导人眼里竟成了洪水猛兽般邪恶的东西,整个社会不敢再碰这部可能引火烧身、敏感的《白鹿原》了。但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把“人民文学奖”授予了《白鹿原》。
拉尔夫·艾默生说:“所有遭到查禁和删除的语言,将回荡在世界每个角落。”不公平对待《白鹿原》的那些领导人早已离开他的位置,被人遗忘了。时光总是把苦难酿成美酒,《白鹿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白鹿原》仍是最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年年被出版社加印。
关于《白鹿原》的删改问题,也值得一提。《白鹿原》的所谓删改,集中在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只要有高格调,文学本无禁忌,许多禁忌是我们自己设置的。食色性也,长期以来,我们禁止写性,避开了人性冲突——灵与肉的冲突,于是我们的文字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而《白鹿原》最具光彩、最惊心动魄的是写礼教与人性,天理与人欲,灵与肉的冲突。比如“黑娃与田小娥的相遇与偷情,是黑暗环境中绽放的人性花朵,尽管带着过分的肉欲色彩,毕竟是以性为武器的反抗”(雷达语)。我看过《白鹿原》的原稿。《当代》编辑部以“应有节制,或把过于直露的性描写化为虚写、淡化”的“审稿意见”,让陈忠实忍痛割爱,删去了不少揭示人性的性描写。我以为对《白鹿原》造成了伤害。
后来,评茅盾文学奖时,又粗暴地令陈忠实再次删节性描写,一批所谓的文学批评家,却干着违背文学规律的蠢事。果然,“干净”的《白鹿原》得了茅奖。
又后来,时过境迁,陈忠实勇敢地以第一版《白鹿原》,取代“干净”后的《白鹿原》。
我曾想:“陈忠实应力争恢复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叙事的初稿《白鹿原》,让读者和评论家来评判二者的差异,公道自在人心。
文学创作需要天赋,需要智慧、文化和思想,有时更需要创新和勇气。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