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cription:路遥和鲁迅、钱钟书等经典作家一起,被认定为最受当代大学生欢迎的十大作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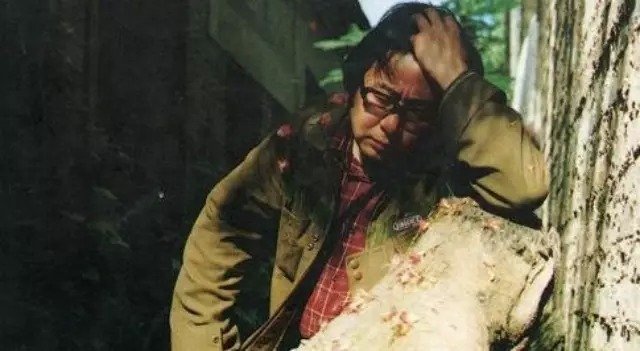
路遥与余华的对峙
编者按
路遥的最高成就止步于《人生》,他前此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都是《人生》的准备,而后此的《平凡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各种评判标准来看都不过是《人生》的“加长版”,这些是否能够支撑路遥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地位,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即将收尾,且不管其收视率是否达到预期,它毕竟承载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今日微信选自《重读路遥》中杨庆祥先生的一篇文章。本书展示一个充满了文学症候学意味的"路遥研究学"。文章作者包括程光炜、李陀、刘禾、蔡翔等人。更有一批80后学者加入,提供了别样的研究思路。
原标题:
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前后“文学场”的历史
文 / 杨庆祥
时至今日,关于路遥的研究和言说似乎越来越具有“仪式”的气氛。在一篇文章中,路遥被认为是一个“点燃了精神之火”的人,在另外一篇很让人怀疑的调查报告中,路遥和鲁迅、钱钟书等经典作家一起,被认定为最受当代大学生欢迎的十大作家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路遥人格和精神力量无以复加的称颂之中,我们似乎隐隐约约嗅到了某种“政治美学”陈旧的气味,路遥成为指责1985年后当代文学大规模实验失败的最“有力”的理由。如此说来当然不是为了像某位先锋批评家所言的要“保卫先锋文学”,也不是为了否认路遥研究的重要性或者否认路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怀疑这种不加任何历史分析的研究方式,它带来的恶果可能与前此一段时间对路遥的“冷落”一样严重,虽然采用的是完全颠倒过来的认知方式。
可以说目前大多数关于路遥的研究文章都是“反历史”的,对于路遥的无缘故的冷落和无条件的吹捧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的态度。路遥既不是当年那种不合潮流的“落后”作家,也不是今天为了应对文学的“贫弱”而搬出来装点门面的“老古董”,路遥是这样一位作家,他非常真实地、没有任何逃避地参与到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中,并为此付出了一位严肃作家应有的力量。因此,如何穿透这二十年来种种言说路遥的话语泡沫逼近历史的“实际”,是本文首先尝试的方向,在此前提下,路遥的自我意识、写作姿态、读者想象都是我深感兴趣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考察“现实主义”这样一种威权话语如何在1985前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场域获得其问题意识并发挥其历史效用,最终,试图为路遥这样一位秉持现实主义写作伦理的作家提供一种合理的文学史定位。
一、 对“现代派文学”的“犹疑”态度
对于1983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界而言,有一个话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怎样去应对和评价“现代派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派”文学在1983年以后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标准,并以此来区分“先进文学”和“落后文学”,甚至是“文学”与“非文学”。在小说界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寻根文学”的提倡和实验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它与文学评论界在1985年左右倡导的“主体论”和“向内转”遥相呼应,似乎在一夜之间,“现代派”文学成为代表中国当代文学最新的也是最成功的一种“方向”。
路遥相当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的文学形势此时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各种文学的新思潮席卷了全国。……文学评论界几乎一窝蜂地用广告的方法扬起漫天黄尘从而弥漫了整个文学界。”(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他丝毫没有掩饰对此的失望情绪,甚至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批评这种现象:“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至今我仍然感到失望。我们常常看到,只要一个风潮到来,一大群批评家都拥挤着争先恐后顺风而跑。听不到抗争和辩论的声音。看不见反叛者。……这种可悲现象引导和诱惑了创作的朝秦暮楚。”(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1页。)路遥的这些判断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处于一种非常焦躁的“加速度”运行之中,不仅各种文学思潮层出不穷,作家的代际更替也非常迅速,在1983年以后,由于大量的西方文学思潮的引入,这种情况更是严重,以致于一位被目为“新潮”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也不禁大发牢骚(新潮批评家黄子平当时有一句话广为流传:“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
如果把路遥的这些带有情绪化的言论和他的写作实践结合起来,很容易造成一种误会,即,路遥是在刻意反抗“现代派”文学的前提下进行其创作实践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路遥对“现代派”文学当然没有“顺风而跑”的认同和承认,但也没有对之进行全盘否定。可以说,路遥对“现代派文学”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这从他的一些言论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说:
就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国出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潮流作品,大多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上成熟,更谈不少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的意义十分重大……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身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样式。(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这一段话大有分析的余地,路遥并没有把“现实主义”和“现代派”进行简单的“二元对立”式的叙述,在他看来,文学形式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他承认“现代派文学”作为一种变革的“文学形式”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所反对的并不是“现代派文学”作品本身(在文艺批评文章《无声的汹涌》里面,路遥高度评价了小说《月亮的环形山》中的语言水平,并称之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从这一点看来路遥同样具有现代派所谓的“语言意识”。见《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64页。),而是批评和创作之间的“名不符实”,在他看来,当时的“现代派作品”不仅是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没有达到可以成为一个“方向”或者“主流”的地步,因此,他反对的是把这种并不成熟和成功的“现代派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方向”和“标准”,进而“排斥”了一些更为成熟的文学表现样式。
对“现代派”文学的这种犹疑和警惕的态度反映出路遥和当时新潮文学界不太一样的文学史观念。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中,“进化论”基本上是一个“共享的”文学史理念,它支撑了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大规模的文学实验和文学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化论”实际上是100年来中国人想象世界同时也是想象文学的最基本的思维模式。路遥身处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自然也逃不脱这种思维的樊笼。但是有趣的是,即使在这种共享的“进化”观念之中,也有显然的区别可以讨论。在1985年以来的“现代派文学”的倡导者和支持者那里,文学的进化所依据的标准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不是小写的“民族国家”,而是大写的“人性”和“人类”。“现代派文学”尤其是其极端形态“先锋文学”正是通过纳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传统而与“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
“如果我不再以中国人自居,而将自己置身于人类之中,那么我说,以汉语形式出现的外国文学哺育我成长,也就可以大言不惭了。所以外国文学给予我继承的权利,而不是借鉴。对我来说继承某种属于卡夫卡的传统,与继承来自鲁迅的传统一样值得标榜,同时也一样必须羞愧”。(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收入《余华作品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因此,构成这些“传统”的必然是“卡夫卡、乔伊斯、普鲁斯特、萨特、加缪、艾略特、尤内斯库、罗布-格里耶、西蒙、福克纳等等”。(余华:《两个问题》,见《我能否相信自己——余华随笔选》,第174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在此,作为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被放置于更高的“进化”的链条上,从而叙述出“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但是在路遥的理解中,“进化”和“变革”虽然都是必需的,但却不一定非要使用一种“西方”的或者“二十世纪”的标准,如果说“现代派”们通过刻意与世界的“接轨”获得了一种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自我意识,那么,路遥正是通过一种刻意的与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认同而获得其自我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遥回到了柳青和《创业史》所代表的文学传统上面。虽然路遥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了包括托尔斯泰、曹雪芹甚至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作家对他的影响(具体论述可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但是,真正称得上是他的文学导师的却只是柳青。在他留下的不到十来篇的文艺随笔中,就有两篇关于柳青的:《病危中的柳青》和《柳青的遗产》。从这两篇极具个人情绪甚至带有传记色彩的短文可以看出,柳青对于路遥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具体到写作的风格、修辞的特色、人物的设计,更包括作家本人的生活方式、人格气质和精神魅力。在《柳青的遗产》的结尾,路遥表达了他对这位作家顶礼膜拜的致敬:“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33页。)以致于有的研究者认为柳青是路遥的“导师”和“教父”。(参见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姚维荣的《永恒的人格力量》,见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第448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
仅仅就路遥和柳青的私谊还是就文人惺惺相惜这些方面来看,我们都不能怀疑路遥热爱柳青的真诚,虽然他在一些场合也毫不犹豫地指出《创业史》一些小小的缺点(比如路遥就曾经指出《创业史》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杨加喜的“出场”过于唐突,没有安排好。见《早晨从中午开始》,第29页。)。但是,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因为在1985年以后的文化语境中,这样充满感情地高度评价一位毛泽东时代的作家实际上是相当不合时宜的,从这一点看来,路遥的这种文化偶像的树立是在表达他的文学姿态,他对柳青的认同,实际上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学遗产的认同。与现代派文学为了确立“新”的文学制度而迫不及待地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一刀两断”的决绝态度不同,路遥表达了对历史连续性更多的尊敬,他认为:“只有在我们民族伟大的历史文化的土壤上产生出真正具有我们自己特性的新文学成果,并让全世界感到耳目一新的时候,我们的现代表现形式的作品也许才会趋向成熟。”(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3页。)在路遥的理解中,这种“新”的文学成果和“现代的表现形式”自然不能由“非本土非民族”的“现代派文学”来承担,而是应该由柳青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来承担。
1985年代强大的“现代派思潮”给“现实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对“现实主义”的话语空间给予了很大的挤压。这么说并不仅仅指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已经遭到普遍的冷落,而且,即使是坚持现实主义的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路遥看来,“农村问题”是他全部创作的主题,而且,“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吗?”(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67页。)非常有意思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往往注意到了路遥关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叉叙述,却没有注意到在路遥的意识里面,“农村”和“城市”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隐喻,直接对应着“中国”和“世界”。路遥对于中国的全部想象都是建立在“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之上,因此,他的现实主义可能是一种带有“农民情绪”的“民族主义”。他非常清醒地利用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及柳青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柳青关于农村变革的书写实际上更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它与毛泽东的政治理念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现实主义”带有实验性质和“反抗现代性”的全球视野。但是,在路遥这里,因为政治实践上的失败,现实主义的空间已经大大缩小,它开始失去其构建一个“新世界”的内涵,而回归到一种比较朴素的、带有原生态的写作观念或者创作手法的意义上去。但是吊诡的是,因为毛泽东时代确立的一些“成规”在1985年代并没有完全祛除,它使“现实主义”在这些“成规”和新的思潮的夹缝中显得暧昧而复杂。这一点,正是我们下面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二、“作家形象”与“写作伦理”的确认
路遥是新时期以来最成功地确立了自我形象的作家之一。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等一系列自传体散文中对于自己“受虐式”的生活和写作方式的“书写”展示给世人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第一要务”的“圣徒”形象,他后来的英年早逝更是加重了他身份的“烈士”(这一说法直接来自于奚密所谓的“诗歌烈士”,见奚密:《从边缘出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意味。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勤劳”和“守成”一直是被赞美的品德,如果为此而献身,则更是能引起同情和尊敬。可能正是基于这种种原因,正如我在本文的开头所言,对路遥的“个人”形象的无限制的赞美简直就成了一种“仪式”,这一“仪式”的神话色彩在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中只有海子可以与之媲美。
而且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迄今为止对路遥个人形象的分析始终没有超出路遥自我设计的范围,具体来说,始终没有超出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塑造的文学“圣徒”和文学“烈士”的形象,从这一点看来路遥比任何一位当代作家都具有“经典化”意识。但是路遥却并非一个先知先觉的作家,他如此孜孜不倦地叙述他的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到并不一定是为了为后人树立一个雕像,而是因为他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的过程中遭受到了非常现实的压力,这些压力一部分来自他内心对某种文学“高度”的向往(所谓的巨著情结),另外一方面则来自当时整个文学形势的变化。正如他所言:“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刻。”(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60页。)从后一个角度来看,《早晨从中午开始》更像是一份“申辩书”,在此路遥不厌其烦地为现实主义的“合法地位”进行了不屈不挠的“申辩”,正是在这样一个“申辩”的过程中,不但一个清晰的“作家形象”被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作家形象”的确立,路遥为我们确认或者说重申了一种“写作的伦理学”。
具体来说,路遥的写作伦理包括身份意识、写作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路遥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似乎带有某种“偏执”,他始终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农民”作家(安本·实在《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中即把路遥定义为“农村作家”。见雷达主编《路遥研究资料》第37页。)。通过这种定位,他不仅坚决地与所谓“新潮”作家区别开来,甚至也不同于包括沈从文、汪曾棋、以及同时代的贾平凹等“乡土作家”的身份。在路遥的理解中,他首先是一个“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其次才是一名“专业作家”。阶级身份高于并决定了他的文化身份,这正是毛泽东和柳青时代遗留下来的一种写作伦理,路遥对柳青最为赞赏的一点就是,这样一位精通各种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路遥:《柳青的遗产》,《路遥文集》第二卷。)可能正是出于这种身份意识,路遥特别强调写作所具有的“体力劳动”的性质,在路遥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随笔中,处处可见到的是因为创作带来的“高强度的”、“密集式”的甚至直接导致“疾病”和“生命危险”的“艰苦劳作”。(比如恶劣的居住环境、非常粗糙简单的饮食,还有病态般的精神紧张等等,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路遥看来,他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是一致的”。他如此急切地意欲填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为了达到其目的,他甚至试图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同一”起来。根据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了完成《平凡的世界》的写作,路遥像他的前辈柳青一样,努力地“深入生活”,“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23页。)为了熟悉煤矿的生活,路遥一度在铜川煤矿生活写作了几年时间。路遥通过这种“重新到位”的方式努力把其所要书写的对象(环境、人物、时代)与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统一起来,作者不仅要写,更重要的是,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这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伦理最本质的内涵,作者的写作并非了确立一个“自我”的存在和“美学观念”,而是为了通过文字这种实践行为,把个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身份认同都统一到一个更高的“整体”中,这一“整体”可以被称之为“生活”、“现实”、“革命”、“社会”等等,但无论修辞如何变换,它都暗示了“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在当代中国所切切要求的道德、政治、美学“三位一体”的历史诉求。
这样一种写作伦理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坚持,实际上,它必须在体制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其系统功能。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史往往被描述成为一个全面断裂和“新变”的文学过程,似乎毛泽东时代确立的文学原则、艺术趣味、文学运行机制在一夜之间就终结了。这实际上有把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产生这种认识的原因在于没有认清话语和现实之间微妙的区别。实际情况是,在1985年代,虽然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体制在话语层面基本上已经面临着全面解体的危险,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层面上,这种文学体制还将借助意识的惯性和政权的稳定性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以路遥为例,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了来自“体制”力量的大力配合。为了让他能更加“深入生活”进行写作,他先后被安排到铜川矿务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到某县武装部院子里“驻扎”,在陕西榆林,包括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都为了他的写作而操劳(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提到当时榆林地区的地委书记霍世仁和行署专员李焕政亲自出面安排他看病就医。后者甚至亲自到厨房为他安排伙食,在“结算房费的时候,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具体参见第87页。)。更饶有意味的是,即使路遥一再抱怨《平凡的世界》遭到了冷遇,但是,它依然以最快的速度被传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完成后立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国听众播出。)和顺利出版,并最终获得中国当代小说的最高奖项。
总而言之,路遥在1985年代虽然在话语的层面遭到了冷遇,但是通过个人实践的努力以及与体制某种“合谋”的关系,他依然可以在非常现实的层面完成其身份意识、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伦理学”上的统一。
在现代写作伦理看来,这样的“同一性”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分裂”(道德与美学的分裂、政治与美学的分裂、个人自我意识和人格的分裂)正是现代写作伦理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路遥难道没有意识到这种分裂的可能性吗?他难道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专业作家”的“自我”实际上离他的“农民”们已经很遥远了?他难道没有意识到当他把农村、煤矿作为需要重返的对象和客体时,他实际上只是在“想象”一种和他并没有关系的生活?无论如何,路遥顽强地坚持着这种统一性,刻意维持着自己的“身份想象”,因此当他偶尔流露出某种智力上的优越感和生活方式上与表现对象(农民)决然不同的“洋派”时(路遥提到他有一些“洋”习惯,比如喜欢喝“雀巢”咖啡和抽高级香烟,喜欢看高水平的足球赛。),他迅速用一种更加“自虐”的方式压制了这种“非同一”的意识。在这样的写作伦理中,高加林就像一个具有“分裂”倾向的“现代派”,在刘巧珍类似于“现实主义”的“完整”和“同一性”面前,显得幼稚而且“单薄”。
布迪厄在《艺术的法则》中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趣味的变革往往建立在作家的写作伦理的变革基础之上,在布迪厄的考察中,波德莱尔等人首先是一种全新的写作伦理的实践者(比如吸食毒品、嫖妓、浪荡),在此基础上才生成不同于其前人的艺术法则(参见布迪厄:《艺术的法则》之“美学革命的伦理学条件”, 刘晖译,第12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对于1985年的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写作伦理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激烈的变化,第三代诗人坐在呼啸的火车上浪迹于全国各地,在成都或者上海廉价的酒吧里面,力比多、酒和女人成为诗歌得以生成的酵母(杨黎用调侃的语气说“第三代诗”的发生其实就是他和万夏在成都一个酒馆里与一个女人相遇后的结果。可参见:杨黎《灿烂》,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对于先锋小说家而言,小说不过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它并不构成历史和现实“真实”的一维,小说(文学)不再担任重建“总体性”的重任,而是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技术操作性”的以“语言”为对象的“职业”。“至此,小说从广大社会阶层共享的普遍的体裁和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迅速转变为专业话语和特殊的体裁”,(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和知识分子》,第108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这一转变带有某种先导性,它“预示了某种社会历史的变迁:即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终于脱离宏大的社会角色,从该阶层的最高职能(承担社会良心)回到最低职能(掌握书面文化)。”(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和知识分子》,第109页。)作家不再是“全知全能”的时代代言人,而不过是一个以语言为加工对象的“手工匠人”罢了。
这种写作伦理和作家形象的变化一方面是出于对毛泽东时代文学体制的“反动”,另外一个方面也呼应了“求新求变”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在此历史语境中,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写作伦理本身或许并不具有多么丰富的生产性,但是,作为一种自我姿态,它暗示了一种多元的历史意识和美学信仰。
三、“传播方式”和“读者想象”
路遥对“现代派”在话语层面的“霸权地位”表达了相当程度的不满,这种不满由于批评界对他的作品的冷淡而加重,他抱怨说:“文学理论仍然大于文学创作。许多评论文章不断重复谈论某一个短篇或者中篇,观点大同小异。”(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60页。)虽然蔡葵、朱寨、曾镇南等人对刚刚出版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评价让路遥稍许感到安慰,但明显的是,与《人生》发表时引起的“轰动”效应相比,“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部书(指《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仍然是被冷落的,包括一些朋友,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63页。)对评论界的失望使路遥产生了某种认同的“焦虑”,他转而把目光投向另一个群体——读者,路遥坦言他之所以能在遭到评论界的冷遇下依然坚持创作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有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1页。)
这段话其实是建立在路遥双重“想象”的基础之上,首先是,他夸大了文学界和批评界对他的“冷落”,从而形成了某种对现代的“憎恨”情绪,把自己想象为一个与“整个文学形势”进行斗争的“孤独者”形象;其次因为这种对批评界“排斥”的心理,他转而对读者产生了顶礼膜拜的情结,读者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值”。路遥的读者意识究竟隐藏着何种历史美学观念?它与1985年代的文学场构成何种对话关系?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在《平凡的世界》发表不久,就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路遥“读者意识”中的“大众化”倾向,他们的主要依据在于,“路遥在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上,还主要是从大众文化的层面上考虑得多一些”。(李继凯:《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文艺争鸣》,1992年第3期。)但是,如果从传播方式看来,路遥的“读者意识”就会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情况。路遥作品的传播方式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通过广播来传播。路遥在不同的场合谈到了他与广播电视的关系,他甚至有一篇专门文章的题目就是《我与广播电视》,根据路遥的叙述,“《人生》发表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播剧,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路遥:《我与广播电视》,《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57页。)同样,他的《平凡的世界》在出版受到阻碍的时候,是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通过电波向“读者们”进行传播的,后来,该作品的第二部、第三部一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广播是一种特别值得讨论和研究的传播方式(已经有学者意识到了现代通讯技术对于毛泽东时代政治统治的突出作用,费正清等人认为:“……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乎是正确的。”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年》,第6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在中国的语境中,它基本上是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应该都记得,来自村头大树或者街道电线杆上“大喇叭”里面的“声音”往往象征着某种无形的权威和压力。在文学传播方面,广播通过“听说读写”一系列的传播、反馈、整合的方式,把匿名的读者和作者都“组织”到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思想”中去。这是现实主义美学在当代中国发挥其功能性效用的特殊方式,包括《欧阳海之歌》、《金光大道》、《西沙之歌》、《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的传播都与此相关。
在1985年代,虽然“喇叭式”的广播作为一种物质事实因为社会的转型已经逐渐消失,但是因为经济的改善,收音机作为最普遍的媒体的普及,用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广播”的功能。具体到小说的传播上,“广播”更强调的是小说的“主题”和“故事情节”,为了达到吸引听众的目的,故事的传奇性和曲折性更容易得到强调,而小说文本独特的语言、修辞和节奏可能被有意无意地过滤掉。通过正规“广播员”“普通话”的规范“解说”,小说(文学)文本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异质性”可能被进一步消除。更重要的是,广播通过一种无形的声音媒质,把作者、读者和小说整合进的实际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正如安德森所言:“有一种同时代的,完全凭借语言……来暗示其存在的特殊类型的共同体。以唱国歌为例,在唱的行为当中蕴含了一种同时性的经验。想像的声音将我们全体连接了起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17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广播”播出时间的一致、播出长度的固定、解说员的确定、普通话的规范性都加强了这种“共同体”经验的延续:听众(读者)和作者(他同时也是听众之一)在收音机之前想象到与他同时分享的是“无数的”的“读者”,这种数量上的庞大感觉带来了美学和道德上的自信心,并进而确认了其作品存在的合理性。对路遥来说:“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向前行走。”(路遥:《我与广播电视》,《路遥文集》第二卷,第457页。)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读者想象”,路遥才不无自豪地宣布:“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能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路遥文集》第二卷,第15页。)
对广播这种传播方式分析可以看出,读者对于路遥来说是一个想象的、可以随时被“召集”起来的“群体”。首先,读者在这里是不可分析、无法讨论、沉默的一个群体,阅读所需要的交流基本上是“单向度”的,虽然《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收到了大约两千份读者来信,但这些信件除了表达对路遥的尊敬和赞美以及询问诸如人生何去何从的幼稚问题之外有何作用?其次,路遥的读者虽然在数量上可能非常庞大,但是,缺少必需的稳定性和持续,路遥的读者绝大部分是“一次性读者”,而且是流动的、业余的。
站在“现代派文学”的立场上当然可以如此指责路遥的“读者想象”,但恰好是这种广泛的、无法区别和具体化的读者群是路遥和他所代表的美学最需要的,读者的出场和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可以对作品进行现代意义上的阅读和建构,而是为一个宏大的“总体性”进行证明。路遥和它的作品所要担当的并非是“交流”和“沟通”的角色,而是“导师”和“引路人”的角色,是“意识形态”借助文学的传声筒试图再次整合和规范社会,树立信仰,给人生、理想、青春和奋斗提供“合理答案”的文学行为学。
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终完成于1988年5月。虽然他借助特殊的传播方式和制度支持获得了一定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它并没有如路遥所盼望和断言的“满足了各个层面的读者”,这不仅是因为1985后“读者”的层次结构越来越复杂,更重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文学场在1985年代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现实主义话语固然借助其制度资源继续在该场域中占有位置,但是由于整个知识气候和社会转型的影响,非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包括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先锋文学)越来越占有着文学场的主导位置。1986是先锋文学开始鼎盛的时期,它获得其话语空间的首要因素就是对路遥所代表的话语和美学的规避,对于先锋文学而言,要想摆脱前此文学所依附的“世俗角色”(道德、政治、历史等等),似乎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回到“语言”和“内心”。先锋文学当然需要读者,但先锋文学的“读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李陀对此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说:“一方面,现代派写作出于反传统、反体制的立场,往往有一种为少数人写作的倾向(这方面他们很自然地接过了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很多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又都和二十世纪刚刚形成的文化市场拼命拉关系(想想毕加索),梦想占有更多的读者。因此,现代主义和市场、读者的关系是相当暧昧和混乱的。”见李陀:《漫谈“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一方面,为了凸显自我的“先锋性”,先锋文学需要“拒斥”一部分读者,而另外一方面,先锋文学又汲汲着力开辟新的读者群体。在1985年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缠绕,比如先锋批评家和作家一边对传统读者的阅读趣味表示蔑视,而同时又为小说的可读性的增强而感到欢欣,即使这种“可读性”与“先锋诉求”有某种不一致的地方。(正如吴亮所指出的,“从1986年起,马原的小说明显地增强了可读性……马原小说的可读性因素是狡猾地利用(或娴熟地运用)了如下的故事情节核——命案、性爱、珍宝,他还在里面制造出各种悬念,渲染气氛,吊人胃口也是他的惯用伎俩”。见吴亮:《马原的叙述圈套》,《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但无论如何,在先锋文学的发生期,如果不对路遥所热爱的“无限的大多数”读者予以排斥和拒绝,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属于先锋文学的“读者圈子”就无法建立起来。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李陀为什么特别强调“友情”在80年代文学中的地位,“另外,把问题缩小,只从文学艺术的创造和发展来说,友情,还有友情形成的特殊空间氛围(真诚、温暖、互相支持,又互相批评)更是一个特别宝贵,甚至必不可少的条件。”(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之《李陀访谈录》,第2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对于李陀所代表的“先锋作家”而言,他们更重视是那些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探讨甚至是责难的“读者”。在这里,“友情”不但指某种特别的人际关系,更指向一种文学生产、运作的机制。这一机制凭借其稳定、持续的具有建设性的传播、阅读、批评,从而形成一个“小而坚固的产业”。
正如李陀所言:“从根本上说,读者是被建构起来的一种存在,阅读不可能有固定的审美标准和价值标准,往往要受时代风尚和主导话语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李陀:《漫谈“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路遥的“读者”和先锋文学的“读者”不仅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想象”,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想象”的背后隐藏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运行机制,在1985年代,这两者借助各自的资源优势,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丰富着80年代文学关于“读者”的想象性建构。
四、结语:作为一种“制度”的“现实主义”
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是,我们在何种意义上来定位路遥的地位和“意义”。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路遥的“经典”地位在于他呕心沥血所完成的“现实主义”长篇著作《平凡的世界》,而也恰好是在这一点上,另外一些研究者表达了截然不同的意见,他们只是非常有限度地承认了《人生》的“文学史地位”(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面没有对《人生》进行论述,只是一笔带过,《平凡的世界》干脆就没有提到。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专门讨论了《人生》,但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平凡的世界》。)。这里凸显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学评价标准、文学史准入原则和差距甚大的美学观念,任何执之一端的看法都可能有失偏颇。站在1985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的”或者“纯美学”的观念来判断路遥,当然会得出路遥并不“经典”的结论,因为路遥的作品并不能给现代批评提供一个“自足”的文本。但是如果站在一种 “泛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来夸大路遥的地位,也同样值得怀疑,因为一个事实是,路遥的最高成就其实止步于《人生》,他前此的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都是《人生》的准备,而后此的《平凡的世界》无论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各种评判标准来看(主题、人物、思想、结构等等)都不过是《人生》的“加长版”,这些是否能够支撑路遥作为一个“经典”作家的地位,还有待时间的考证。
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在世界范围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原则在二十世纪的确呈现逐渐衰弱的趋势,这与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非理性思潮的凸显,政治学上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经济上中产阶级的壮大密切相关。罗曼·罗兰可能代表着现实主义在西方最后的“辉煌”,但他不久就遭到了普鲁斯特强烈的抨击:“罗曼·罗兰先生着力刻画一个较精确的形象,写出来的却是一部既精致又矫饰的作品……这种艺术愈是浅薄,不真诚,庸俗,这种艺术也就愈是世俗性的。”(【法】马塞尔·普鲁斯特:《驳圣伯夫》,王道乾译,第22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罗曼·罗兰基本上被剔除出了西方经典作家的系列(参见沈志明译《一天上午的回忆——驳圣伯夫》,“译序”,第9、1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他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在于抽样调查以及对出版的考察,比如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就没有收入罗曼·罗兰的作品。)。对于中国和前苏联而言,现实主义借助政权的力量获得一度的“威权地位”,并形成一种特殊形态(有时候被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形态改写了现实主义的内容和形式,并把现实主义从一种“美学观念”变为一种“制度实践”,这种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要求写作者在美学、道德、政治、伦理上都实践着“同一性”,而且,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还通过其特殊的认证原则、传播方式把这种“同一性”撒播到读者群体中,试图构建一个“坚不可摧”的文化“共同体”。
路遥的独特意义正在于此,他是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最后的一次扎实的实践,在一个“同一性”的制度、文化开始分裂的特殊历史时期,他坚持着这种“同一性”的想象,并把它转化为现实的文学行为。他代表的美学观念和文学实践因而具有过渡性质,不可避免地带有“挽歌”的色彩,但也因此具有“仪式”气氛。如果对路遥所实践的“现实主义”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认识到作为“制度”的现实主义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意识到了所谓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实是一种“制度”的胜利,现实主义的衰弱其实是一种“制度”的衰弱,那么,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就不是对路遥的“冷落”,而更需要警惕对“路遥”的“神圣化”,因为这种“神圣化”在肯定路遥的美学的同时也在肯定着与这种美学同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制度”,这样可能会带来文学中新的威权统治,从而钳制着来之不易的可怜的文学和美学的自由和多元化的可能。(《南方文坛》)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